阅读:0
听报道

编者按:
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的文化有何不同?银河系的命运是什么?外星人存在吗?星际旅行的可能性有多大?且看《天问》专栏与英国皇家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詹姆斯·宾尼(James Binney)“谈天说地”。
采访 | 李颖
转录 | Anna Mao
翻译 | 钱磊
责编 | 吕浩然
● ● ●
《天问》:你之前来过中国么?
宾尼:来过。2010年,我曾在北京大学科维里研究所的一个暑期学校讲课;2013年,我在北京做了一个报告,并参加了在丽江举办的一个国际天文联合会研讨会。
《天问》:你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如何?
宾尼:令人惊叹!按照转变的速度和程度,从任何真正意义上来讲,她都不是如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午间在学校用收音机收听关于文化大革命最新进展的新闻,很显然,她有过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她现在看起来非常像西方世界。不知道我这么说,人们会不会高兴,但确实是这样的。而且,现今有那么多中国人,这是一个可畏的事实。
《天问》:你指的是人口?
宾尼:这是我们那个时代和我子女这个时代的事实。我女儿现在在(浙江)诸暨教英语,以便提高她的中文水平。她一直在学中文,我想她是对的,她认识到在她这一代,中国会变得重要。
《天问》:学习中文?
宾尼:她和她男朋友一起学中文。是的,这很难,就像学英语对于中国人很难一样,但是我想,或许(学中文)要更难一点,因为中文的书写系统很难。
《天问》:你是怎么对天文学产生兴趣的?
宾尼:实际上,我并没有(对天文学感兴趣),而是对物理感兴趣。我在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学业导师(director of studies)是托尼·休伊什(Tony Hewish,197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译者注)。他发现了脉冲星,但他却是一位物理学家,战后进入射电天文学领域。
1970年前后,射电天文学似乎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我在1971年毕业,这(射电天文学)看起来是应该进入的领域或者说应该前进的方向,而粒子物理学看起来陷入了死胡同:有一个问题太难解决——我完全错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在被标准模型解决,但本科生不知道所有他们应该知道的内容,所以托尼·休伊什让我去找丹尼斯·席艾玛(Dennis Sciama, 图1),他成为了我的导师。
正因如此,我可以说是一个进入了天体物理领域的物理学家,这是一个使用物理的好地方,有很多你可以研究的、有趣的问题。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我不是天文学家,而是对天体系统感兴趣的物理学家,因为这是你可以玩物理(play with physics)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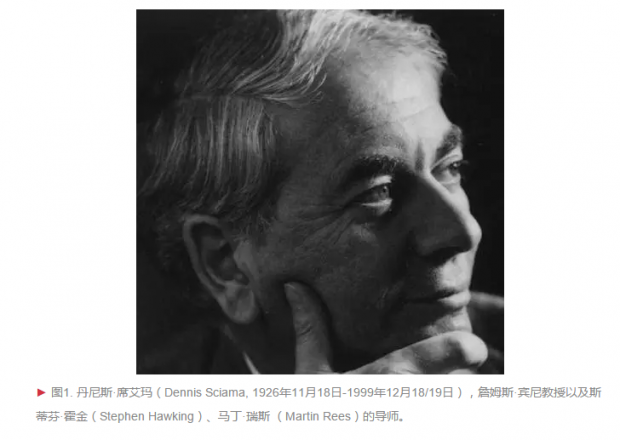
《天问》:所以,你的主要兴趣是物理?
宾尼:是的,而且显然,如果你做这颗行星上能做的物理,那么它只是物理学的子集。宇宙中有更多的物理,那对物理学家而言是个好地方,而且显然,这种立场,这种对天文学的思考方法已经完全成为标准,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尤其如此。
当我开始(研究生涯)时,天文系通常是和物理系分离的,并不是物理系的一部分。但当高能物理学家意识到宇宙学是严肃的高能物理学的用武之地时,情况就变了:所有物理系都必须有很强的天文研究组,而且这些研究组中不是只有几个人;很多物理系的天文研究组是最大的研究组,这些物理系的组成完全改变了。我想,我在大学院系(university departments)的这些年间,天文和物理的关系完全改变了。
《天问》:你在剑桥获得本科学位,又在牛津拿到了博士学位,进而在那任教。您怎么比较这两所学校呢?
宾尼:牛津相对而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剑桥相对而言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换句话说,牛津有一个更集中的、更受控的系统,就像你在中国会发现的那样;而剑桥则更随意、更自由。我想,在零级近似上可以说是这是二者之间的不同。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在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中有微妙的不同。当我刚到牛津时,我感觉有点受打击:牛津的建筑和剑桥的相比是如此死板。
《天问》: 你能否简短介绍您在星系天文学中的研究?
宾尼:我们试图理解星系如何能存在:为什么有星系?为什么当你观察宇宙时你看到的是星系,而不是无尽的恒星?这个问题与星系实际如何产生结构(structured)、如何形成、如何像机器一样运行等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你理解一个星系是如何形成(put together)以及如何像机器一样运行的,那么你也会理解它是如何组建(assembled)的。
现在,我和我的研究组正致力于理解我们自己的星系(银河系)是如何形成(built)的。我们的星系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机器,由不同部分组成。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不能直接看见的暗物质,我们只能间接探测到它。理解它如何产生结构就已经是一个难题了,而之后我们还必须理解它如何像机器一样运行,这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如何随时间演化的,随后向我们阐释它如何形成(put together)的问题。
我研究的题目是星系形成,这将我带到了河外星系的动力学领域,我想这是我首先产生了影响的领域。在过去十年,我回过头来研究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不过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星系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关。
《天问》:你认为有趣么?
宾尼:我成为牛津大学教员是在三十六年前,而我的第一篇文章则发表于1974年,那已经是四十三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写了四十三年的文章,已经写了数百篇。显然,我仍然觉得这有趣。
因为,我觉得物理是美妙的。因为,通过物理研究你可以理解那些完全在人类经验之外的事物,在巨大时空尺度上运行的事物,你可以理解它们是如何运行的。你可以计算,可以精确预测那些你能测量的事物,而且这些预测通常很好。
在现代世界中我们对技术奇迹和科学的力量见得太多(very blasé)。惊人的是,用数学你能预测会发生什么、某人会测量到什么,这件事是行得通的,并且很优美!人们谈论艺术,我只是觉得艺术是好的,我一点也不反对它,我也时不时去画廊观摩,偶尔去看戏剧,但和科学相比,艺术是没意思的(feeble),科学要比艺术美妙得多。
《天问》:你认为星系碰撞是否有可能?
宾尼:是的,这是真实发生的。实际上,银河系未来将会与我们最大的邻居——仙女座星系碰撞,在大约三十亿年内,两个星系将会运动到一起。目前,我们对于这在多久之后会发生必然是有点模糊的,因为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仙女座星系垂直于我们视线方向的运动速度,但我们知道银河系正在向仙女座星系运动,且在三十亿年内二者会运动到一起,并且与其合并。
《天问》: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银河系星系会和另外一个星系合并?
宾尼:是的,银河系将不复存在,在短于我们星系年龄的时标内。
《天问》:那太可怕了!
宾尼:不!可能与你的想象的合并有些不同,我们星系中的一千亿颗恒星会向仙女座星系下落,与仙女座星系中的一千亿颗恒星混在一起,其中大约仅有一两颗恒星会和其它恒星碰撞。这会类似一种行进队列表演,一个单元队列穿过另一个。但两个星系会被完全摧毁并重构为一个新的星系,这会是一个椭圆星系,它会慢慢死去,因为新的恒星形成或多或少会停止。
《天问》:两个临近的星系可能会合并,那么所有的星系最终也会合并成一个星系么?
宾尼:不会,因为宇宙膨胀足够快,能保持星系彼此分开。但是,如果宇宙膨胀加速像超新星数据表明的那样(我完全不确定是否如此,但科学界相信是这样的),未来就是极端孤立(extreme isolation)的,我们本星系群的星系会聚到一起,变成一个大星系,我们将可能会变得孤立于宇宙中大部分其它星系,因为它们被推开了——在大尺度上,(由于暗能量)力是具有排斥性、而不是吸引性的,其它星系会被越来越快地推离我们,我们在观察它们时,它们也会变得越来越红,最终我们会和它们失去联系。
《天问》:你是说我们的星系?
宾尼:我们的星系还会在它原来的位置。但如果你一千亿年(a hundred gigayears)后再往外看,可能会真正看到黑暗,除非你有台巨大的望远镜,也仅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少的、非常红的天体,除此之外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我们自己星系中的恒星。

《天问》:你写了很多本书,其中一些成为了大学教科书,比如《星系天文学》和《星系动力学》。你是否把这些书看作您最伟大的成就?
宾尼:我不知道。虽然写这些书可能耗时超过十年之久,但它们只是讲述人们已经知道的知识和信息,我只是传播而已。
而做研究则必须做出新的贡献,我的小小愿望是:我的一些研究并不是很显然——如果没有我,这些结果其他人并不会马上做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这涉及到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贡献的问题。首先,你是否说过正确的、之前不知道的东西?如果答案为是,进一步的判断标准是不管你说了没有,会不会有其他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出?如果是,那你的贡献其实无足轻重。
但我仍希望我做的东西中的一些,如果没有我其他人会花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因为这些问题人们长时间没有关注,然后才意识到需要严肃对待。这些我和其他人在认识上的时间延迟使我认为这些结果并不是完全明显的。所以虽然我写的一些书确实有用,但我还是更希望我的一些文章有比书重要的贡献,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
《天问》:公众通常对“是否有外星人?”感兴趣,你的意见是什么?
宾尼:我认为地外文明显然会遍地开花。我们的星系盘中的大多数恒星都有有行星绕行。并且,在类似太阳系这样的行星系统中有处于椭圆轨道中的类似木星的天体,这对生命是不好的。但我们知道类似太阳的恒星有很多,在我们的星系盘中有大约一千亿颗与太阳类似的恒星,所以即使它们中的1%有类似我们的行星系统(可能实际要高一些),也会有十亿颗,我们的星系是我们所在宇宙区域可见的十亿个类似星系中的一个,而最好的科学证据表明宇宙是无限的,我们只能看见它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宇宙中必然有百亿亿个类似我们的行星系统。为什么生命的出现不是一个普通过程?或许需要运气,或许一千颗合适的行星只有一颗拥有细菌,然后是恐龙等等。(即使这样)我们仍然留下了惊人的巨大数目。有人会问:如果这些文明存在,为什么它们还没有来过这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
这个问题,某次我和一个本科生一起思考,我们研究了在太阳系之间星际旅行的前景,游戏规则是假设所有物理所允许的事都可以做,工程师可以非常高效。所以,如果你说我们想进行星际旅行,有足够多的钱和合理数量的时间,我们还是有很大可能会做到,当然,除非被物理禁止。如果物理不允许,比如反引力或其它违背物理的事物,那么无论花多少钱,也什么都不会发生。
于是,我们坐下来想想这种情况下的星际旅行。随后,我非常惊讶于它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我们认为看起来基本上被物理禁止的每件事,都有足够的物理原因,为什么它行不通,它令人惊奇。
我们都坐在我们的椅子上,受到重力(无论什么物体,重力加速度g都是9.8m/s2 )的束缚,如果你以重力加速度(g)在你的火箭里加速一年,你会达到相对论性运动,而持续两三年,你就达到很高的相对论性运动了。其优美之处在于,相对论预言的时间膨胀或空间收缩(依赖于你怎么看待它)使得我们和一些近邻星系之间的距离减小。
所以,如果你能建造一颗火箭以1g或g/2加速,那么在这颗火箭中你会非常舒服,悠闲地喝着咖啡,感觉完全正常;一两年之内,你会发现到目的地恒星的距离会小得可以忽略:按你自己的表,你一定可以在十年之内到达那里。这些是对星际旅行的可行性论证,听上去没有问题,对吧?你只需要去实施,让工程师参与,把活儿干了。
好,当你开始思考质-能守恒和加速过程的影响时,你可以得出结论:显然,用现有的任何自携燃料的火箭都无法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得不被来自地球的能量束推动,随后就有各种与衍射有关的问题产生,这些都使得星际旅行非常、非常难以实现。
即使你能加速,即使你可以被推动达到相对论性速度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另外的恒星,你也会遇到需要减速以(实现)顺利造访的问题,你必须以加速度g减速数年。这意味着这么做没有希望,因为我们关于火箭原理的结论会不起作用。你可能必须通过这类能量束使你减速,这再次碰到衍射的问题。
同时可以想见:某些外星人(可能)已经以相对论性速度经过地球,拍了一些漂亮的照片,但它们不可能造访地球。没有我们的帮助,它们确实无法造访。所以我认为SETI研究、寻找地外智慧生命重要,因为这些文明就在那儿,但它们不可能造访过地球。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外星人的任何事情?不,我们会知道它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倾听它们的信号,也必须发射我们的信号。我们的信号还没有走得非常远,也有一些人在收听外星信号。以目前的技术来看,接收外星信号极端困难,因为设备对非常远的信号没有足够的灵敏度,但我仍认为我们会在接下来数百年内和这些文明进行联系。
在接下来几百年,如果我们没有获知其他文明的存在我才会感到非常奇怪,这甚至很有可能发生在未来五年。显然,这对于人类可能是变革性的,但情况是,这些文明可能会在数光年之外,信号从我们传到它们会花费数年、数十年,这意味着对话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仍会有对话。这要花费时间——文明不总是以建造北京的速度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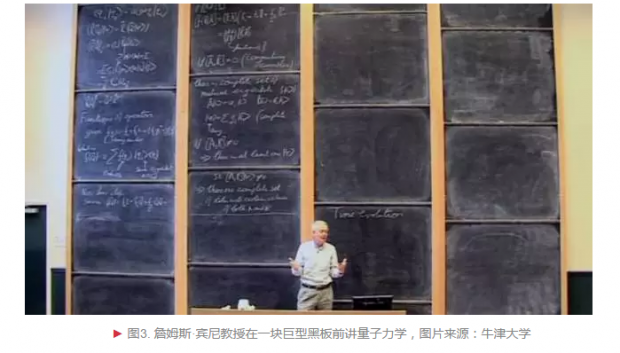
《天问》:像《星际穿越》、《地心历险记》这类电影中的场景又是否会发生呢?
宾尼:像《星球大战》那样的事不会发生。我做这个本科课题是因为我认为像《星球大战》这种事在两千年后的社会学中(the sociology of two thousand years forwards)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元素。因为,如果人们进行相对论性旅行,那么他们可能会完全把时序搞乱:如果你进入这颗以1g 加速的卓越的火箭,花了十年访问某颗近邻恒星然后返程,你将变老二十岁,或者变老十岁,无论如何会是一个合理的数。
但地球上的人则会变老几百岁,回到未来数百年的地球,这应该很有趣,对吧?在《星球大战》中,他们完全没有涉及相对论性旅行这个方面的内容,事实上,他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光速还快,但他们对于人们的钟以不同速率运动没有任何疑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样的旅行速度可能是合理的。实际上,物理并不允许相对论性旅行,和同时性有关的事都没有实际意义。
《天问》:回到教育方面,在你看来,教学的本质是什么?
宾尼:我参与教学已经超过四十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非常擅长教学(图3和图4),但是我感觉强烈的是用现在的知识重写一切的重要性。我认为课程和人们教授核心物理内容的方法太传统了,是基于历史的。人类发展知识的速度令人困惑,自十七世纪末的科学革命(可以说始于牛津)以来,对物质世界理解的发展速度不仅快,而且还以令人畏惧的速度加速发展,我们掌握的知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一个真正的问题:要保持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站上知识的舞台,使他们可以开始做自己的工作,在合理的时间内消除无知,到那时他们有差不多二十五岁,仍然年轻充满活力,如果你一直坚持用过去的误解和混乱的思考、看待事物的糟糕方式浪费他们的时间,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分析和重写他们继承下来的知识以使它们尽可能精简而高效。这就是我尝试做的事,但同时,科学革命的核心原理是任何事情都不应依赖于权威,每件事都应该被质疑,每个论断都应该最终被某些实验演示证明。所以,我相信对于教育,不能牺牲严谨、不能含糊和毛躁、不能把物理变成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有纪律的,基于数学、实验和定量论断的不讲情面类型的学科。我认为在教学的时候,更不应该偷工减料。
另一方面,你必须以最简洁的方式写出公式,你必须找到核心,这又是另外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变成物理学家,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记忆力,我不喜欢那种你必须了解很多早期信息的学科。物理非常好,因为你需要知道的非常有限,你只需要掌握至关重要的知识点,然后由此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重构你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教师的工作是找出重点——随着知识增长,学生应该掌握的重点可能会变化——让他们理解怎么做。由这些重点,你需要开始解决一些特定问题,做一些特定的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由于其自身知识的原因,每一代人都要重做一遍。作为一名教师,我自己对物理的理解必然会牵涉到我的教学当中,在我教学的这些年,我的网站上有很多我长时间没有教过的课程讲义,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我会重写这些讲义,因为我已经认为那些是垃圾:做得不好,低效,没有好处。
《天问》:你曾在普林斯顿教过书?
宾尼:是的,但非常短暂。
《天问》:然后你又到牛津教学。你怎么比较这两座城市?或者说,如何看待英美之间的不同?
宾尼:普林斯顿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镇,完全被大学主导,我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年,我讨厌它,因为它太沉闷了。我在普林斯顿第一年没有和任何人太熟,大西洋两岸也存在着巨大文化差异。
在我来到普林斯顿之前,我住在德国,也暂住过瑞士,因为语言的差异,我感受到了它与英国的不同。但当我二十五岁第一次到美国时我发现,对于英国人来说,美国要比德国不同得多,因为在欧洲之内有文化相似性,有基本共识(assumptions),这在美国已经行不通了。
我还发现,没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甚至无法理解我说的话,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会问某人去某地的方向,或者我会在加油站和某人谈论某事,我发现他们无法理解我的意思,即使我再次重复我的初衷,他们还是不能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奇特的耻辱:如果你试图说德语或法语表达某事,尽管对方不理解你,你可能会理解为你没有把德语或法语说得足够好,你必须更努力地尝试。但当你对一个人说自己的母语时,情况就有一些微妙的不同——词汇有差异,就像当我想把我的衣服拿去洗的时候我会问洗衣店(the launderette),而在美国你必须问投币机(coin-op,coin-operator),不管怎么说,那是二十世纪70年代的情况。
美国人还非常严肃。我从没觉得普林斯顿是家——在我去那里时,我以为我会永远待在那里。英国在二十世纪70年代非常糟糕,这个国家似乎经济上有点走下坡路,有灾难的感觉,政府运行得不是太好,贸易联盟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艰难。所以在我去普林斯顿时,我想我会永远待在美国。
但出乎意料的是,牛津有个工作职位,我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对这种回家的方式很高兴,但也发现我很怀念普林斯顿,因为它在学术上是杰出的,我学到了很多。我也想念牛津的事物,尽管相比于美国的很多优质大学,它们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是落伍和缓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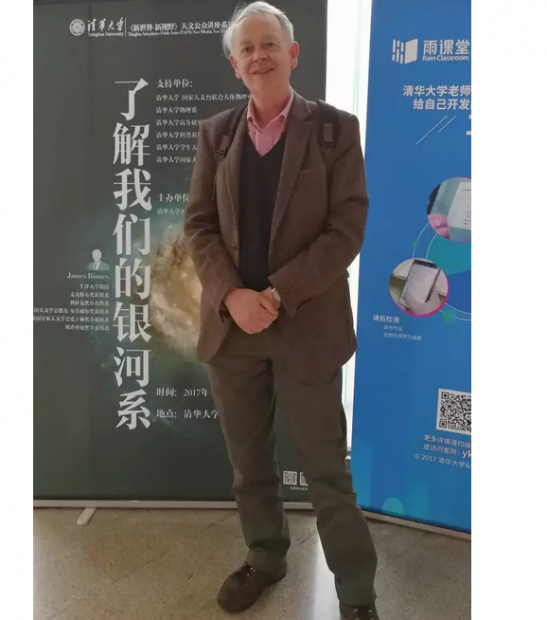
► 图4. 詹姆斯·宾尼教授在他清华大学的公共讲座《了解我们的银河系》的海报前,摄影:毛淑德,2017年3月30日。
《天问》:最后,你对可能对天文感兴趣的学生有没有什么建议?
宾尼:学习更多的物理和更多的数学知识。对于我来说,在做物理时关键的事情总是思考真正发生的是什么,并尝试将其从数学中想象出来。你也需要掌握数学公式。学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想象他们尝试讨论的物理过程。
不仅如此,我确实认为,如果你想成为天文学家,你需要真正掌握物理,因为大多数天文学家其实并不是天文学家,而是天体物理学家,而且越来越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些人得到了很多惊人的数据。另一方面,使得到这些数据成为可能的是那些仪器制造者,他们是物理学家或工程师。无论如何,他们不是天文学家。
另一方面,对观测到的恒星、星系、宇宙,无论对于任何物理理解的梳理都是天体物理学的范畴,它是物理在数据分析、解释中的应用。所以,以现今的视角来看经典天文学变成了废话。我想说的是,对于只是经典天文学家的那些天文学家,几无用武之地了。
注:本文系詹姆斯·宾尼于2017年3月底作为中国科学院特聘教授访问中国期间采访时所做。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