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格蕾丝(《知识分子》科学新闻实验室特邀作者)
翻译 | 郭 剑
责编 | 黄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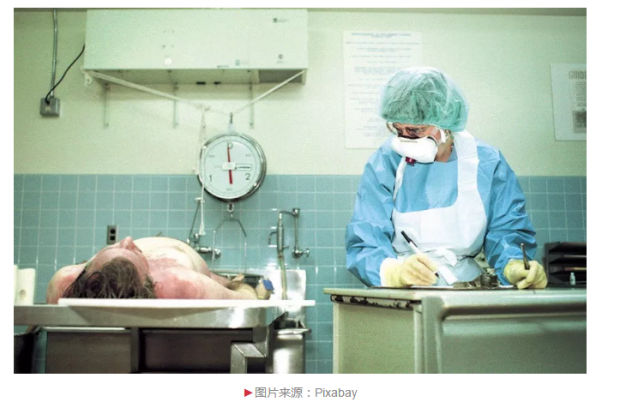
2014年在危地马拉挖掘点的第三天,我们被带到了山坡上另外一个地方,每人发了一把铁铲。前几天我们工作过的坟墓,是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FAFG)的专业法医考古学家们提前替我们开掘过的。今天不一样——我们要以挖掘的方式自行寻找那些还没被打开过的秘密坟墓。
“我们怎么知道在哪里挖?”我的一位同学问道。
“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当地人中,有一些是危地马拉内战期间被关在政府集中营里的囚犯,”我们田野学校的主任解释说,“他们有关于埋尸处的记忆。”
另外一位田野学校的同学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是一名考古学研究生,曾在加拿大做过合同考古学家。“为什么我们不使用探地雷达寻找坟墓呢?”他问道,“从那些人看到尸体被埋至今,地表肯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探地雷达并非法医考古领域的新技术;事实上,作为一种常见的、被广泛接受的工具,考古学家们使用探地雷达已经至少有20年了。但是它价格昂贵,以至于对FAFG来说,并不是合理利用资源的好选择,田野学校主任如此解释道。除此之外,到达发掘地点已经很困难了。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在崎岖的路面上走上几公里,翻过山坡,才能到达地点。
FAFG所工作的大部分地点都是这样的:只能徒步到达。每天早上我们必须将所有的设备运送到现场,然后傍晚再运回去,以免它们被盗。
那还是在早晨,因此空气寒凉,不过我们费力地在坚硬的地面上开掘没多久,就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这种随意挖掘寻找秘密坟墓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该在何时停止。有时候你不停地挖不停地挖,却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是学生,你就得一直挖,直到有负责人告诉你该停止了,才算结束。
有时候直到用铲子实际击中了骨头,你才意识到其实已经找到了。在寻找骨头时候,你可能已经损坏了它们。
当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坐在土坑旁休息时,我身旁一位女性对正在挖掘的人大声喊道:嘿!嘿!嘿!
他们意外地把一块头骨甩进了坑边的土堆里,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大家都停了下来。铲子被放在了一边。我们拿出刷子和抹子,开始工作。
旧的范式
在法医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分析严重依赖于人类的观察。一位专家查看“证据”,然后用他的“专业知识”加以“解释”。专家们通过个人经验和导师专家的培训来获得知识,而导师专家们的知识也是通过个人经验和导师培训获得,如此类推。
不幸的是,很多技术和方法从未得到过科学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家从来没有能够确定这些技术或方法是否真正可行。科学家们使用这些技术就好像它们已经被科学验证过了一样,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
一些学科在有效性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字迹分析、咬痕分析、血溅分析、头发分析等等。即使是测谎仪,就是那种已经存在了超过80年的著名的“测谎”机器,其有效性仍然无法验证。在美国,测谎结果极富争议,以至于许多州拒绝让它们作为证据进入法庭。
此外,即便某项技术是有效的,但只要涉及到人(专业知识),认知偏见就会存在。“认知偏见”是由于个人主观信念而导致的“思维错误”或“对理性的偏离”。通常,提供分析的科学家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有认知偏见。
在美国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是2004年涉及到俄勒冈州一位名叫布兰登·梅菲尔德的律师的案例。梅菲尔德被指控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起恐怖主义爆炸事件有关,因为他的指纹跟爆炸现场一件物证上留下的部分指纹“吻合”。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监禁,尽管西班牙当局通知了FBI他们认为这一匹配是“阴性”的,并且他们已经有了其他在押的嫌疑人。
最初,FBI声称梅菲尔德的指纹与犯罪现场未知的部分指纹之间的匹配是“100%确认的”。后来,FBI的发言人承认梅菲尔德的指纹跟未知的部分指纹并非完全匹配;实际上,其他19名可能的嫌疑人的指纹和犯罪现场的部分指纹也有相似之处。梅菲尔德最终被释放了。很多人认为,认知偏见在梅菲尔德被捕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布兰登·梅菲尔德是穆斯林,许多美国人将“穆斯林”与“恐怖分子”等同起来。这就是认知偏见。
新领域
1983年,美国法医学院前院长安东尼·龙各提在《法医学杂志》(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上写道:“按照定义,能够成为‘法医学’的学科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现在也无法确定,有哪些目前的或未来的专业不能变成法医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这些话很有先见之明。自那时以来,已经出现了数十个新的法医学领域。数字法医学——数码设备上的证据恢复和分析——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出现。紧接着,数字法医学也涵盖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他逐渐流行起来的设备。野生动物法医学出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法医护理在1991年被美国法医学院确认为一个专业,尽管护士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性侵、虐待儿童和其他暴力犯罪的证据。国际兽医法医学协会成立于2008年。法医兽医负责调查驯化动物(主要是宠物)相关的犯罪活动,比如有组织的斗狗和斗鸡——这两种行为在美国都是非法的。
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学科附带上“法医”这个词,那就意味着来自该学科的知识已经或者即将可以用来解释犯罪活动中的证据:法医会计、核法医学、法医病毒学。
法医学在未来可能会延续这一趋势:创建新的法医学领域,来调查新领域里的犯罪。加密货币犯罪已经发生,这就需要加密货币法医学。外层空间犯罪,则需要拥有独特技能的调查员。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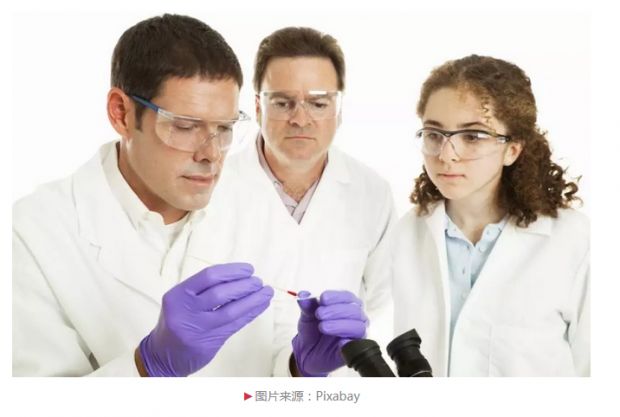
一种新的范式
那么像认知偏见这样随着新的子领域的创建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应对呢?虽然创建新的子领域将帮助我们对抗新型犯罪,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法医学中已经存在的问题:认知偏见、尚未被验证的方法等等。法医学领域本身需要对科学家们“做”科学的方式进行重大改进。
美国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创造了“范式转变”一词,来描述科学家们在某些科学领域/学科内的进步。这些进步是指,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和“做科学”的方式。
库恩在他1957年的著作《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中使用了“范式转变”这个词来描述十六世纪天文学领域发生的事情。当时尼古拉斯·哥白尼公布了他的太阳系日心说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太阳存在于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转。在这个模型问世之前,天文学家们遵循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该模型认为地球处于太阳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地球旋转。
库恩表示,太阳系的日心说模型并没有立即受到欢迎。相反,科学家们花费了数十载的时间,来研究和测试新模型是否比旧模型能更好地预测天文现象。第谷·布拉赫做了观察,约翰尼斯·开普勒做了数学计算。最终,科学家们长达80年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新的范式比起旧的范式,能对天空中行星的位置做出更好的预测。之后又过了50年,这种新的范式才被普遍接受。库恩认为这一横跨了120多年的事件,是一场“经典的范式转变”。
越来越多的法医学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人,认为法医学需要一个范式转变,一种法医学家“做科学”的方式的重大转变。法医学中的许多专业人员现在更多地关注该领域内的“科学过程”:验证技术、制定标准、识别认知偏见。
理想情况下,未来的法医学将更少依赖“人的专业知识”,更多依靠以验证过的技术和明确的操作标准为基础的一种概率框架。事实上,已经有几个法医学领域正在向概率框架迈进了。
那么,“概率框架”究竟是什么意思?
概率框架
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大多数证据都有其内在的多样性。没有两个破碎的窗户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打破的。没有两个鞋印——即使是来自同一只鞋——是完全一样的。同一个人的两次录音,也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存在某些规律,但从犯罪现场收集的数据往往是“连续的”(沿着某个频谱的无限可能的状况),而不是“离散的”(单独的、有限的、可数的)。
然而在美国,许多法医学家被要求就证据做出论断时,好像它们是“离散数据”而不是“连续数据”一样。在美国,法医学家在法庭作证时是“专家证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七条(“意见和专家证言”)指出,“专家证人”“以意见的形式或以其他方式”作证。专家证人提供的证词,应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该证据;基于充分的事实或数据;是可靠原则和方法的产物。证据规则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及专家证人必须将连续数据转化为离散数据,或将科学概率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绝对结论。
伦纳德·威尔士博士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曾在2008年作为专家证人证明被告是否有能力出庭受审。他随后告诉《华盛顿邮报》:“他们要求你确定一些你无法确定的事情。”
另一方面,“概率框架”承认连续数据内在的多样性。相对于告诉法庭“是、否、不确定”,一个概率框架能产生如下结果:“证据来自被告的可能性,比来自其他来源的可能性高100倍”。
“我工作中遵循的框架是概率性的。我出庭作证时,曾经向陪审员解释这一点,但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理解。许多人似乎都有数学恐惧症。”阿斯顿大学语音法医学副教授杰弗里·斯图尔特·莫里森博士说,“陪审员想要简单的答案。简单的答案是‘是的,就是他。相信我,我是一位专家。’冤案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法医学的未来还包括了另一个当前趋势的延续:从严重依赖人类感知和培训的旧范式,缓慢转变为使用大数据和复杂统计建模的新范式。
新范式的阻力
“法医学的范式转变至今仍然不完整,但我认为确实取得了进展。”莫里森说。“有很多阻力。很少有人改变他们的范式。这是有原因的。如果人们非常非常愿意改变他们的范式,并且一直变,那么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范式的转变往往发生在科学家无法忽视的“危机”出现之时。通常,首先是一名科学家做出了新发现,而旧范式无法对新发现做出解释。接着,该领域的其他科学家会通过实验和新理论来探索这个新的发现,这反过来又引出了更多旧范式无法解释的发现。很快,就出现了一场“危机”——领域内大多数的科学家都认识到了旧的范式并不奏效,但仍有很多人不愿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之后,这个领域会分裂成两类实践者:那些遵循旧思维方式的人和那些遵循新思维方式的人。
在法医学中,“发现”认知偏见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几种不同的法医技术缺乏科学验证,也是一个问题。此外,科学家正在研究统计模型,以更准确地解读DNA证据和评估指纹的独特性。
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写的那样,“尽管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年长者和经验丰富者,可能会无限期抵抗新范式,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会受影响。信念的改变一次会涉及到几个人,直到最后的坚守者离世,整个行业将再次实践一个单一的但已不同的范式。”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40年前随着计算机的兴起而开始的现行法医学范式的转变,应该在另一个40年后能够完成。整个法医学行业再次以单一范式实践,还可能需要再一个40年。尽管这一转变始于我们的有生之年,但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它完成的那一天。
新范式,旧问题?
那天在危地马拉,在作为小组成员寻找未开启的秘密坟墓之时,我并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正的工作属于哪种“范式”。我们手里有铲子,面前有需要挖掘的泥土。当你所做的一切都花费金钱和时间,而且在这些资源都极其有限的时候,你很难有心思去操心比眼前任务更大的哲学框架。我们在那里是为了在田野学校结束前记录和回收尽可能多的遗体。
之后的某天,我开始思考科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鸿沟。不是仅在法医学范畴,而是整个科学。也许是我们的整个生活——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即使在法医学向新范式的转变完成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仍将存在。我是指,科学家们在有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时有可能做到的,与在有限时间和金钱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做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法医学的未来将在不同的时间抵达不同的地点。不过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怕是永远都会存在。
关于作者
格蕾丝是美国的自由职业科普作者。她在匹兹堡大学主修写作和人类学,后来获得写作硕士学位。格蕾丝和她先生现在住在美国西北部。他们有三只猫,一只鹦鹉。
译名对照表
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 Forensic Anthropology Foundation of
Guatemala
布兰登·梅菲尔德 Brandon Mayfield
安东尼·龙各提 Anthony Longhetti
美国法医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
国际兽医法医学协会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Forensic Science
Association
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范式转变 paradigm shift
尼古拉斯·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托勒密 Ptolemy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约翰尼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U.S.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意见和专家证言 Opinions and Expert Testimony
伦纳德·威尔士 Leonard Welsh
语音法医学 Forensic Speech Science
阿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杰佛里·斯图尔特·莫里森 Geoffrey Stewart Morrison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