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pexels
2022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50岁,他想解答一个自非典时开始,已经困扰了自己近20年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着无数患者生死的难题。
因为经费的不足,这个研究只是刚开了头。一位同事告诉他,有一笔科研基金,最高资助金额可达每年500万,持续五年,也许他可以申请试试。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吴骊珠一直梦想着再现光合作用的伟大过程。早在1771年科学家就发现植物的光合作用,但直到20世纪人类才利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技术手段进行光合作用研究。
自然界的光合作用是在生物体光合蛋白膜上进行的化学反应,而吴骊珠要做的是在生物环境之外,通过识别和协同形成结构和功能集成的人工光合系统,在温和条件下实现“圣杯”的化学反应。期待通过持续研究,人类不但掌握在现在看来仍然神秘的植物光化学过程,并且知道如何比自然更加高效地获取所需产品。倘若如此,即使在遥远的将来,煤炭石油的供应完全枯竭,人类文明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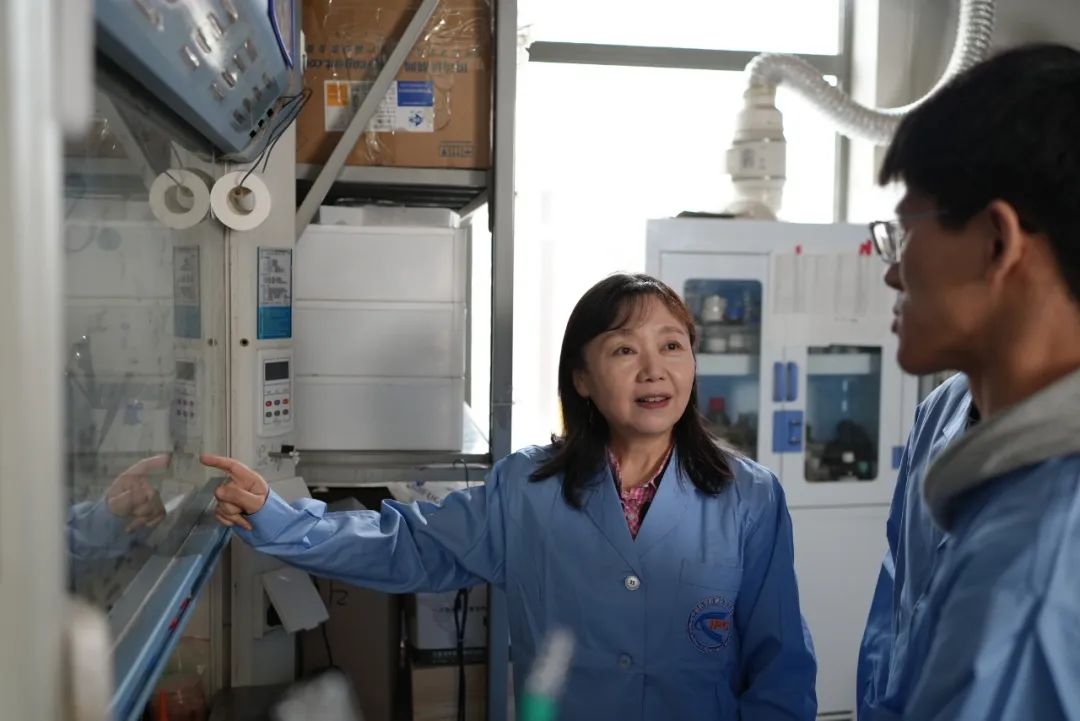
新基石研究员吴骊珠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祁海则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操控免疫记忆之道,让人类能够抵御复杂环境中的各种病毒,治愈自身免疫的顽疾,还能改良和完善现有各种疫苗。他也坦承,“我还没有看到确切的路径,也不知道跳一跳是不是能够得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于洪涛都认为,他关于“基因非整倍性问题”的研究,在传统的资助体系里是拿不到资助的。因为那是一个曾有几代科学家进行尝试,最终也没有解决的问题。
而北京大学化学生物学系主任陈鹏想要做的是:实现“癌症疫苗的精准设计”,但他也知道,虽然前景诱人,但这种突破专业界限的研究不太容易得到支持。
最疯狂的冒险
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人会见识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抗生素拯救无数生命,人均寿命快速增长,诸多疾病被攻克。而1970年之后,真正改变世界的似乎只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今年一月,《自然》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分析了1945到2010年间的4500万篇论文和390万个专利,构造了一套评价系统。研究者们发现,几十年来,各个领域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突破性都在下降。像双螺旋结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这类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今天变得少之又少,科学家在一个稳定知识体系中添砖加瓦,少有颠覆性的贡献。
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原创性、颠覆性的基础研究作用更为关键。过去中国科技发展是引进吸收、跟踪跟进的模式,可以依靠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今天,随着科技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科技需要更多原创性的研究,而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仍是我们的“短板”。
自去年开始,腾讯公司决定在10年内投入100亿发起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致力于支持最聪明、最有成就、也是最胆大的一批青壮年科学家,探索人类未达之境。
应邀者云集。正值事业的黄金时期,创造力达到了巅峰,有能力又有意愿去做出原始创新的科学家,在中国不在少数。
今年年初,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第一批资助名单揭晓,包括曹彬、吴骊珠、祁海、于洪涛、陈鹏在内的58位科学家入选。首批“新基石研究员”以中青年科学家为主,平均年龄48岁,其中包括8位“80后”,最年轻的年仅38岁。

新基石研究员陈鹏
和此前多数资助计划不同的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选人不选项目”。这意味着不对科学家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必须拿出成果的期限。
他们每人每年将获得300万(理论类)或500万(实验类)的资助,持续5年,甚至在资助期满后如通过评估,还可以获得续期资助。
这是中国科学家的中坚一代,他们大多在90年代就读大学,有着扎实的学术训练,后来去海外名校读博或者做博后。他们的事业上升期正好处在国际学术交流最密切的年代,十多年国内外学习的积累让他们年纪轻轻就已做出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有了国际瞩目的影响,甚至有些人已经解出过“圣杯”级别的学科难题。
在新基石项目评选之前,很多人已经拿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长江学者,在国际顶刊当编委,还曾获得过霍华德·休斯(HHMI)研究员项目的认可。但于他们而言,此次申请新基石的项目,仍然是他们在科学上疯狂的一次冒险。
华东师范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刘钢敬佩张益唐那种契而不舍的数学家,他有过读博期间研究18个月毫无进展,几乎对自己丧失信心的经历。这一次,他决定选择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项目,他解释:“因为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并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它很重要”。

新基石研究员刘钢
申请计划中,刘钢列出了一系列令他“魂牵梦绕”的问题,也是令评委们感受到了这位80后年轻人对整个领域认识的问题。一位评委提到,“这些问题只要能够开一个口子,哪怕不是完全解决,也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于洪涛本来也有更“安全”的备选,但他选择了风险最大、最难的一条路。
他的研究方向是基因非整倍性问题——90%的肿瘤都有非整倍性,如果能把这个共同的弱点找出来,靶向进攻这个弱点,有可能治愈很多不同种类的肿瘤。
这是一个既重要又困难的问题。肿瘤虽然大多都有基因非整倍性,但现在还没有找到共性的原因,如果每个肿瘤非整倍性都是由不同原因导致,那整个研究方向就成了沙上建塔。除此外,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这个方向的探索,但目前,把正常细胞变为非整倍性的实验只能在体外,没有直接观察体内肿瘤成长过程。

新基石研究员于洪涛
在新基石申请的答辩现场,评委们也提出了异议,部分评委觉得这个研究方向是做不成的。几代科学家都曾做出尝试,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新基石项目对野心和勇气的肯定落到了实处,于洪涛涉险过关。
相比疯狂,祁海更喜欢白日梦这个词,他自认是个追随直觉和兴趣多于理性抉择的人。在他的研究生涯里,好奇心经常驱使他用不同于其他科学家的方式提出问题。
祁海想研究的是记忆B细胞。记忆B细胞是获得性免疫的关键,能记下接触过的病毒的抗原,从而帮助人更好抵御病毒。
谈及这项研究的难度,祁海坦承不确定性很大。“我们研究大脑对T细胞、B细胞的影响,对免疫应答的影响。免疫系统就够复杂了,神经系统至少是同样复杂,甚至更复杂,把这两个系统放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
多位新基石研究员都提到:研究结果的不可预知性,是科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那里往往蕴涵着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方向。
复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张远波倾向于一种看法:未知分成两类,一种是已知的未知,还有一种是未知的未知。科研瞄准的目标都是已知的未知,我们甚至没法想象未知的未知是什么样,但那可能是我们真正想要到达的地方。
对张远波来说,能不能达成目标不是最重要的,失败或者说试错在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中本就不可避免,这是基础研究的规律。“任何基础研究都有这样一个困境,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路走得通走不通。”
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于洪涛也坚信,研究的每一步都不会浪费。“如果你在认为有意义的方向,走出了一步,即便没有达成,即便最终是另一个人在你的基础上取得了成功,那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你是这一切的基石。”于洪涛说。
是浪漫的,也是富于责任的
科学不仅仅是浪漫的,也是富于责任的。
让曹彬无法忘怀的一个场景是,2020年,他和因新冠去世的病人家属谈话,“家属问原因,实际上,医生已经用尽了我们所有已知的医学知识和手段,但病人还是去世了,有些临床现象是我们能解释的,但还有一些是解释不了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近20年之久。2003年,刚刚结束了住院医师培训的年轻的呼吸科医生曹彬遭遇了非典,病毒引发的严重肺炎让他印象深刻。

新基石研究员曹彬
这些严重肺炎中,最神秘和可怕的是患者快速又突然的病情变化,本来人好好的,忽然之间,白肺、全身脏器功能障碍。这种功能障碍,被称之为脓毒症(Sepsis),“以往大家在谈到脓毒症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治疗选择是抗菌素,但如果引发肺炎的是病毒,抗菌素是不行的”,曹彬解释:“之前的共识或者指南,都没有关注到,病毒其实也可以引起脓毒症。”
在眼睁睁看着病人死亡的挫败中,曹彬决定投身研究死亡率超过50%的脓毒症。曹彬逐渐梳理清楚了自己想做什么——把病毒性的脓毒症和细菌性脓毒症做一个区分,搞清楚“临床表现不同之外更深层次的不同,机制上的不同,找到不同的治疗方法来改变病人的愈后……”
2020年,曹彬和他的团队对此的思考《新冠病毒和病毒性脓毒症:临床发现和科学假说》发表在《柳叶刀》上。
之后,曹彬和同事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做动物模型,在实验动物身上观察到了病毒感染与细菌感染造成的临床表现、脏器损伤的种类和程度都是不同的。因为经费问题,他们的下一步研究一度被搁置了下来。
“那是一项需要很长时间和大量的琐碎工作的研究,千头万绪,如同警察在繁多的线索中破案”,这位医生科学家介绍,“要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当中去锁定最关键的环节,寻找最重要的致病机制,然后将其截断,那将是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前途未卜”。
然而,“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人去做,才能使病人有更多存活的希望”。
曹彬打算在新基石研究员计划的资助之下继续他的研究,他说,“我是个医生,支撑我进行这项病毒脓毒症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每天接触到的病人,哪怕能降低一点点死亡率,我想,也是有价值的。”
陈鹏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科学家特有的责任感,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人类历史应该抱有的一种责任。他经常向自己的学生提到,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青霉素,有了青霉素之后,很多感染性疾病人们就不再害怕了,而这个世纪,如何摘掉肿瘤身上“致命疾病”的帽子,攻克癌症,从一定程度上,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身上的责任。
也是这种责任,支撑着祁海“在一个可能是黑黢黢的小屋里跑一块胶,观察上面出现的一个很微弱的条带……”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个微弱的条带,后面证明的是“一个可能改变了某种疾病治疗方式的基因的某种表现形式”,而更多的情况下,它们仅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条带而已,最多是告诉你此路不通。
一次次碰壁后,祁海会不气馁地调整方向,继续前行,直到真正“做出可以改变现状的工作。”

新基石研究员祁海
祁海认为,入选新基石研究员计划对他而言,不仅仅是获得了资金的支持那么简单 ,“当你有这样的资源,当你看到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你会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如果我有能力,但是没有去花时间、花力气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辜负了自己所拥有的机会和条件,我们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不尽力呢?”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

新基石研究员张远波
那么,这群人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真正突破一个从前没人做过的难题,在国际的舞台上,趟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陈鹏兴奋地提到,“我们现在找到了那个0,还需要从0到1,这很难,也许是十年以上的漫漫长路,然而,基础科学需要的便是原创的思想,而现在国家也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没有理由不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最终,我们希望真正解决一些问题,能够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或是在各自领域的科学发展中留下一个印记”,陈鹏感慨。
78年前,范内瓦·布什在他那份被誉为是“改变美国历史”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将基础研究置于至高地位,认为它是新知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头,是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保障。
他说,“基础研究会带来新知识。它提供的是科学资本,是所有实际知识应用的源头活水。新产品和新工艺并非完全成熟。它们都建立于新的原理和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原理和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
虽然没有直接的产出,但如果没有基础研究,“一个依靠别国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也会非常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潘建伟曾经提到,“科学界一直期待,有强度足够的稳定资助项目,支持科学家能够长时间专注自己的兴趣,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探索有风险、有希望的方向”,而作为社会资金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更具有灵活性,既是稳定的源头活水,又能为专注自由探索的科学家雪中送炭。
提到自己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于洪涛认为: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刘钢觉得,“从中可以看出腾讯的远瞻性,不仅仅重视实际应用,还重视基础研究,而且非常重视”。祁海则分析道:“腾讯所做的这样一个资助科学家的项目,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因为真正优秀的原创科学发现是能够创造人类历史的,而这些投入正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着这种改变。”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作为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的一部分,期望通过鼓励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解决“认识自己”和“认识自然”的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源动力。
吴骊珠说: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企业,去鼓励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这对腾讯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新基石研究员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腾讯在这个时间去做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不仅是在资助人,资助项目,也是在培养人!在我们从事这些研究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并有所作为。”
吴骊珠还提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曹怡老师和张宝文老师带领团队,巧妙利用光异构化反应缩短了维生素D3合成路线,大大降低了副产物的生成。这样一个光化学反应从实验室做出来,到成功转让给企业,革新了当时人们的认识,使我国打破国外垄断,成为掌握维生素D3先进生产技术的国家。这项研究和从事这些研究的科研人员,对于当时求学的我们这些学生来说,都有莫大的鼓舞作用。
而曹彬则提到了过去的三年,如果我们的这项研究能够有所突破,面对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疾病,甚至未来面对重大的疫情,整个生态就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三年时间,大家经历了一种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毒所带来的恐惧、紧张和焦虑,如果我们对病毒引起的疾病可以了解更多,当我们人类下次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就能更从容一些。”
这位医生科学家说:“最大的恐惧来自未知,从容地应对未知,需要我们更好的认知,这便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和理由”。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张远波谈起了数学家希尔伯特在1930年退休感言的结束语。如同那句,我们登山,是因为山就在那里;人类的科研探索,是因为问题就在那里,而我们必须,也必将知道。
至今,这句话镌刻在希尔伯特的墓碑上,代表着一代代数学家的追求,而且,“这可能是我们所有探索未知的这些科研人员共同的想法。”张远波说。
注:2023年4月10日起至5月31日,2023年度“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开放申报。2023年度“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计划资助不超过50人。申报人可通过项目官网()了解如细分领域、申报指南、常见问题解答等信息,并进行申报。本年度“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名单将于2023年第四季度公布。
参考文献:
1. Yu, Hongbin, Yang Yang, Hailong Wang, Qian Tan, Mian Chin, Robert C. Levy, Lorraine A. Remer, Steven J. Smith, Tianle Yuan, and Yingxi Shi.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and trends of
1.Izabella Kaminska.(Sep,13,2017)'s not about the low hanging fruit, it's about the ideas. financial times
2. Tyler Cowen.(Jan,29, 2011).Innovation Is Doing Little for Incomes. The New York Times
3.刘云.(2019).专访于洪涛:我们培养的是下一代科学家,不是下一代技术员.《都市快报》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