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奥本海默》电影
撰文|张天祁 李珊珊
“像一个命运尽在掌握的男人”。
1945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一位同事这样形容控制中心掩体外的奥本海默。
这个带着微妙的原子弹试验场“霸总”气质的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了“原子弹之父”,人们评价他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却不得不终身承受这个行为带来的惩罚。
不仅如此,这位盗火者的传记作家还认为他是美国科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几乎是美国的最后一位“具有科学背景的大公共知识分子”,自他之后,科学家几乎退化成了技术专家,他们不敢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只能在技术上做出批评,因而也就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1942年,38岁的奥本海默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3年,20亿美元,他们制造出了一种大规模屠杀性武器,赢得了美国人在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赌博,把人类战争推向了新的原子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几十数百居民的城市可以在顷刻间被摧毁,人类将可以轻易拥有毁灭世界的能力。
短暂的成功喜悦过后,这个男人感受到的是长久的恐惧。两颗原子弹投在了广岛和长崎,几十万人死亡,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毛骨悚然”成真了,“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他向总统杜鲁门抱怨。
自那之后,这个打开了魔盒的男人试图亲手去关上这个魔盒——利用“原子弹之父”的声誉,他反对威力更大的氢弹的研究,呼吁、游说,希望达成一个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建立一个制约核武器发展的国际组织,梦想着唤醒人们来“废除核武器”……他越来越不是政客们希望的形象了,他严重影响政客们的计划了,这便有了旨在除掉他的那场“听证会”。
在那里,这个男人几乎是被脱光了衣服面对着一群全副武装的对手,然后,所有的记录被公布于众,他被毁了。
这场掺杂了政治斗争、个人恩怨、冷战、麦卡锡主义的“奥本海默事件”,几乎是20世纪美国的最大冤案之一。然而,自那之后,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物理学家一度变成了弃子,他生活在“一个人的囚牢”,一直到去世。有人评价这个骄傲的男人时,说他“非常谦逊”。
奥本海默死于1967年,2006年,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传记奖,今天,以这本书为主要蓝本的电影《奥本海默》正在上映。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记者曾向前述《奥本海默传》作者之一凯·伯德(Kai Bird)提问: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吗?科学事实是否仍在因为政治利益而被歪曲?
“恐怕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伯德回答。
也许,这个回答,便是今天的我们,重新回顾奥本海默故事的原因。我们回顾这段往事,希望70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希望如这位“原子弹之父”所言:让原子弹“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也是一个巨大的希望”,为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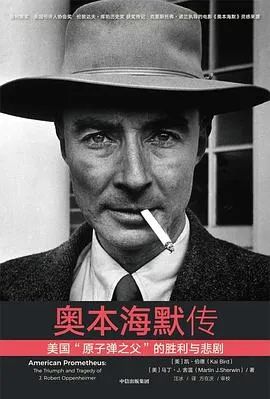
《奥本海默传》封面,中信出版社出版。
先知奥本海默
“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一场有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参加的战争,让告别了冷战阴影多年的人们再次想起了被核战争支配的恐惧。这种世界核战的威胁,早在80年前,早在原子弹出现之前,在奥本海默建立的那个小镇,人们便早已意识到了。
1943年,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工厂成立第二年,像“科学事业上的父亲”一样的玻尔来访。玻尔启发了奥本海默,他们都相信,一种以核能为基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箭在弦上,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却也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希望”,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是带来一个开放、和平的新世界的希望。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一个黑暗森林假说认为,文明可以靠信息阻隔带来的威慑来维持和平。但当时的奥本海默和玻尔想到的是另一种方式,用信任来维持和平——核武器下的和平,需要每个国家都必须确信没有潜在的敌人在暗中储备这种武器,那便需要充分的透明度和信任。
玻尔说:那是个“开放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国际核查人员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军事和工业设施,并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学进展。奥本海默显然对此深以为然,他深信自己正在创造的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将击败法西斯,终结所有战争,建立一种新的文明。
让原子弹来终结战争,为人类带来永久和平,这个信念深深扎根在了奥本海默的心中,即便在原子弹研发最艰苦的那些岁月里,这一点也从未动摇。在原子弹试爆前夕,一群年轻人开始从伦理角度质疑是否要继续开发这种“小装置”,奥本海默加入了那场辩论,他用柔和的声音在这场讨论中“占了上风”,因为“很多未成年男孩都会因它而保住性命”。
奥本海默“就像天使一样,真实又诚实,他不会出错……我相信他”,一位参加过那场讨论的物理学家回忆道。
1945年夏天,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当时的记者采访中,奥本海默淡然地回答:爆炸的景象是“可怕的”,但也“并不全是令人沮丧的”。多年后,回忆那个场景,奥本海默提到了自己在《薄伽梵歌》中读到过的句子“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这个句子,被用在了诺兰电影的一个限制级镜头中。
那之后的两周里,据当时的同事回忆,兴高采烈狂欢的年轻同事中,奥本海默变得异常安静,甚至有人记得他会边抽着烟斗边说“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好像在宣布死讯。
一些迹象显示,对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奥本海默并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也许这是因为他深知,需要一种方法让大家知道这种新武器的威力。为了更好地进行这场演示,在当时,科学家们曾向军方提出过各种意见,比如:邀请各国代表参观一次试爆告诉大家新武器的威力;将投弹点选在一个偏远的兵工厂;甚至,在投弹前知会当地政府,让平民先躲起来以减少伤亡。很显然,这些建议都被无视了。
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8月9日,另一颗原子弹投在了长崎。同日,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报告说,奥本海默“精神崩溃了”。
资料显示,在1945年年末的一段时间,奥本海默确实处于一种强烈的失望和悲痛的状态,当年11月,他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我们使劲摇晃一颗硕果累累的果树,从树上掉下了雷达和原子弹。整个(战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对现有知识进行既疯狂又无情的剥削。”
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讲,曼哈顿计划所取得的成就,那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300年来物理学的顶峰”,然而也令物理学元气大伤。
不过,这种悲伤没有维持太久,因为他需要振作起来,去实现梦想中的那个开放、互信的和平新世界。
天真的原子科学家
在战争中,争论一种武器是否比另一种武器更不道德是愚蠢的…..
二战后,原子科学家们从胜利带来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开始反思原子能的危险,追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最为热衷于进行这场控核运动的人,正是那群参加了曼哈顿计划,亲手缔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先是在洛斯阿拉莫斯,然后是芝加哥、橡树岭……到1945年11月——第一颗原子弹投入战场后的第三个月,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家组织,原子科学家联合会成立,很快,这个组织又更名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FAS),但宗旨始终未变,即:致力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FAS展开的积极游说下,美国设立了非军方管理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委员会(AEC),AEC成立了一个由9名杰出科学家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GAC),其中奥本海默担任主席。
似乎科学家运动在民用核能上获得了初步胜利,但胜利的感受很短暂。AEC名义上是民事委员会,但却建立了一个军事联络委员会,实际上在发挥军事用途。科学家们争取来的原子能法案,在国会的修改下,几乎变成了他们反对的军方方案。
相比其他原子科学家,奥本海默承担的是更沉重的任务,他要讨论的是更为政治敏感的核武器问题,面对的是更为狡猾的军方和政客高层。
在此之前,奥本海默已经见识到了和政客交流的难度。1945年底,他在杜鲁门面前脱口而出“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鲜血”,双方不欢而散。
1946年初,奥本海默和同事利连索尔经过两个月的合作,提出了“艾奇逊-利连索尔计划”。虽然没有奥本海默的名字,但内容是由奥本海默一力主导的。
这份计划坚信美国的核垄断不会持续太久,在此基础上 ,奥本海默提出了一种超前又天真的方案。他设计了一种国际控制原子能的方法,各国将放弃部分主权,将其原子科学信息和材料交给这个全球机构,该机构随后将控制地球上的所有铀,使其仅用于和平目的。既提供了针对原子武器的安全保障,又提供了电力来源。
这个以世界、以全人类为坐标的长远计划,刚上交就遇到了政客的黑手。国务卿伯恩斯在收到这份材料当晚就找到了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巴鲁克,他们两人都在铀矿上有大量投资。铀矿共有,他们第一个不同意。
伯恩斯说服总统,将“艾奇逊-利连索尔计划”扭曲成了“巴鲁克计划,将一个去中心的原子能国际机构变成了一个保证美国核垄断的机构。这个计划很快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计划无疾而终。
这次计划的失败令奥本海默心灰意冷,准备回归他的物理,“物理学和物理教学曾是我的生活,而现在它们似乎无关紧要了”。
这一切,直到1949年,苏联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再次振奋起来,觉得机会来了,苏联掌握了核武器技术,这就意味着过分的保密已经没必要。
然而,政客们却不是这么想的,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想到的对苏联核武器的应对就是:核弹产量,以及,尽快研发氢弹。两个超级大国进入了核武器的军备竞赛阶段。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很多,原子弹的最大爆炸威力很难超过50万吨,而氢弹这类热核武器几乎没有固定的上限。氢弹的出现可能带来对人类无差别的大屠杀,甚至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这让奥本海默感到恐惧,决定阻止政府尝试氢弹的研究。
奥本海默提交了一份涉及氢弹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氢弹,他聪明地选择了技术上的批评:批评氢弹“设计模糊,性能不确定”。而且由于生产一公斤氚需要放弃大约 70 公斤钚的生产,研发氢弹会拖慢原子弹武库扩充的速度。策略上讲,美国武库中的大量原子弹足以应对苏联。因此,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报复,氢弹都是不必要的存在。
然而,天真的他还是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出发点。他附加了一份“少数派附件”,在那份附件中指责氢弹 "它的存在和对其构造的了解对整个人类都是一种危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必然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这些道义上的指摘,成了这份报告在政客眼里的弱点,审核氢弹问题的委员会表示,“在战争中,争论一种武器是否比另一种武器更不道德是愚蠢的…..战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耻辱必须落在发起敌对行动的国家身上。”
最后,杜鲁门在相关会议上只和利连索尔谈了7分钟,当他确认苏联有研发氢弹的可能后,他宣称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并且禁止所有科学家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1952年美国引爆了世界第一颗氢弹,1953年,苏联成功试爆氢弹。就这样,与科学家期盼的和平愿景相比,美国的军方和政客选择了确保美苏相互毁灭,哪怕这可能终结人类文明。原子科学家曾盼望的和平时代没有来临,奥本海默与玻尔最初开放世界设想已经被两极格局的现实无情摧毁。
听证会,一次公开处刑
国家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年代,攻击一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永远是最方便的泼脏水手段。
反对氢弹失败的奥本海默,在政府中的地位逐渐边缘。1953年后,他的对手,氢弹的热情支持者施特劳斯成为了ACE主席。
在政府中被逐渐边缘化之后,奥本海默还一直试图利用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的声望和地位,从内部影响国家安全机构。他的老朋友们和他的弟弟都劝他,这是一场徒劳的赌博,但奥本海默坚持发声。
天真的奥本海默,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
今时不同往日,战争时期政府需要科学家在技术上的帮助,也需要树立科学偶像以凝聚人心,奥本海默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对政策的影响力。但在冷战期间,政府更忌惮科学家独立于政府的影响力。现在政府需要的不仅是能干活的科学家,更是听话的科学家。
奥本海默身在美国体制内,却坚持着知识分子的做事原则,在公共领域不断发声、批评国家政策,这很难说到底是有勇气还是太天真。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环境下,他遭到攻击和清洗完全不奇怪。
从更长的时间段看,美国官僚系统一直希望消除科学家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使他们成为为政府服务、只讲技术的专家,而战争时期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从曼哈顿计划开始,美国政府就致力于打造一种新的科学家角色。艾森豪威尔 1946 年分发的一份备忘录标题最恰当地总结了这个目标:“科学技术资源作为军事资产。”
要实现这个目标,拿最有威望的奥本海默开刀虽然有风险,但回报也是可观的。FBI主管胡佛的说法表明了政府现在对科学家的态度,“科学家们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个人感觉,他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
奥本海默作为最杰出的科学家,曾经被推到民族英雄甚至神话的高度,现在是时候被打落凡间了。
在那个国家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年代,攻击一个人对国家的忠诚,永远是最方便的泼脏水手段。
由于反对氢弹的立场,奥本海默早就被麦卡锡盯上。1953年5月,麦卡锡曾向FBI局长胡佛表示要调查奥本海默。麦卡锡还声称,政府里的苏联间谍让氢弹计划推迟了十八个月。“我们的国家很可能会因为拖延而灭亡。请问是谁造成的?是忠诚的美国人,还是我们政府的叛徒?”
不等麦卡锡发难,奥本海默已经遭到了指控。1953 年 11 月 7 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主任博登写信指控海默很可能是“苏联特工”,建议剥夺他接触机密的安全许可。一场秘密听证会开始了。
这是场不公平的听证会,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
起草对奥本海默指控信的AEC法律官员格林表示,听证会的“预定目标”就是发现奥本海默存在安全风险。根据格林的说法,为达成这一目标,施特劳斯和FBI主管胡佛都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有反对奥本海默倾向”的强硬派被选入委员会。
尽管从法律上讲,这次听证会只是一次调查。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不仅是审判,还是对奥本海默公共身份蓄谋已久的一次处刑。
奥本海默的影响力让他的对手们极为恼火。他们明白,就算失去了政府公职,奥本海默还是会以大科学家的身份继续批评氢弹。想让奥本海默彻底闭嘴,就要彻底摧毁奥本海默作为一个科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人的信誉和威望。
就像一位AEC官员对“氢弹之父”泰勒曾说过的那样,关键是要”在(奥本海默)自己的教堂里脱光他的衣服”。让奥本海默下台是不够的,还要拿掉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光环,让他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
这本来应该是一次秘密听证会,但听证会前,对奥本海默的指控信和他的回复全文都已经被泄露给了《纽约时报》。听证会开始后,内容也被奥本海默的对手随意透露给记者。秘密听证会变成了全国直播的媒体狂欢。
隐私在这场听证会中是不存在的,听证会掌握着对奥本海默多年调查和窃听的完整资料。奥本海默被迫承认自己和琼·塔特洛克的婚外情。被当庭盘问“她为什么必须见到你?”“你和她过夜了,是吗?”
奥本海默还要回答他身边哪些人是共产党,哪些人是同情者。如果说了,奥本海默就是背叛朋友,这大大折损他的个人信誉。但如果不说,听证会就会坐实他的不忠诚。
原本有着出色表达能力的奥本海默,在律师罗布审犯人一样地连续盘问下经常陷入混乱。
他曾在纠正自己说法时提到“我想我是个白痴”,这句简单的自嘲被他的对手大加演绎,用来羞辱奥本海默。媒体报道中,奥本海默说这句话时“蜷着身子,双手紧握,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过去媒体上仿佛智慧化身一般,随口引用《薄伽梵歌》、解释量子力学奥本海默,现在却自相矛盾、自认白痴。
本该保密的听证会文字记录,在听证会结束后也被施特劳斯借故公开。奥本海默受到的种种指控,在庭审过程中的每一次羞辱,以及几乎整个人生的档案都暴露在外,任由公众审视。
可以说,即使听证会能证明奥本海默的清白,暴露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奥本海默,也不可能再变回那个神话一般的科学家了。
直到听证会结束,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奥本海默不忠诚,但他的安全许可仍被剥夺。奥本海默的公共角色也被打垮了,尽管他还能继续公开露面,发表科学和哲学讲座,但他在公共领域中已经销声匿迹。这次听证会成功把他从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当时的一位记者曾经对这种变化表示过震惊,他说:“奥本海默曾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钦佩的人之一,被人引用、拍照、咨询、颂扬,几乎被神化为一个全新的英雄神话原型——科学和智慧的英雄,新原子时代的开创者和活生生的象征……突然间他消失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过多少年,他显然被人遗忘了。”
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
今天对于科学家的不信任,部分可以追溯到当年奥本海默受到的公开羞辱。
奥本海默案给整个科学界带来了恐惧。科学家们意识到,即使是像奥本海默这样的国家英雄,也会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存在疑虑,就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1957年至1959年间担任总统科学顾问的小詹姆斯·R·基利安 (James R. Killian Jr.) 博士在十多年后回顾此案时说道,“奥本海默案最可怕的方面是它造成的恐惧……技术建议如果不支持当前的某些军事或政治政策,可能会受到谴责。”
奥本海默身上有着一代原子科学家的缩影。他们曾经有着崇高而远大的愿景,坚信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能够控制原子能的世界政府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但这种国际主义期盼却在冷战的浅滩上触礁。
随着战后美苏关系的紧张日渐加剧,美国对安全的国家安全追求逐渐陷入偏执,仍对联合国控制原子能抱有期望的原子科学家们,成了被怀疑和被打压的对象。科学的理想,最终败给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怀抱国际主义理想的科学家们是最好的替罪羊。在政府和军方授意的宣传攻势下,科学家的形象和共产主义者、间谍、叛徒联系起来,公众越来越认为理论物理学家是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1954 年,一位科学家向 AEC 抱怨,“公众媒体的夸大报道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科学家作为一个阶层非常不可靠,而且许多人都不忠诚。”
一些学术和政府科学机构支持也这种红色恐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其工作人员制定了忠诚承诺书,并解雇了许多拒绝签署的人,而 AEC 则启动了新一轮的安全审查听证会,以清除涉嫌颠覆的人员。
打压的另一面是收编。冷战时期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扩张给科学界带来了大量经费,也给物理学家提供了稳定高薪的就业机会。军事相关的研究一度主导了物理学家的就业,而想要得到这样的工作,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都要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需要放弃那些体制不认可的言论、行为和人际关系。
美国需要科学家的知识,但不需要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按照政府的官方说法,科学家表达科学意见的自由应该受到尊重。但事实上,只有当科学意见与道德和政治问题无关时,科学家才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被迫在公共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噤声后,美国科学家群体出现了分裂。
一部分科学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一面,退化成了技术专家。在核威慑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基本前提的情况下,科学家只在技术上提出建议。哪怕不认同现行政策的科学家,也不敢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只能在技术上做出批评。相应地,他们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那些仍然独立于体制,坚持道德批判的科学家则发现,很快发现自己已经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甚至受到同行的排斥,被政府甚至同行看作活动家而非科学家。他们的同行已经学会区分哪些科学是不挑战冷战红线的、被容许的。
而科学家在公共问题,尤其是原子科学问题上的意见,本来对公众是非常宝贵的。由于原子试验的保密性质,得到原子试验报道机会的媒体,往往是和政府、军方的合作者,报道的内容也要受到审查。
那些基于对健康危害的担心,对原子试验的质疑则没有被报道,甚至干脆被抹黑成有叛国嫌疑。未能获得公众关注,也没有进一步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
比如内华达州试验场的一次核试验后,犹他州境内放射性沉降物肉眼可见。但报道中出现的却是“不到100辆汽车需要清洗”"AEC人员平息犹他州辐射疾病的报道 "“信息人员试图平息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这类官方辟谣。直到7年后,AEC才承认当时犹他州测出了“人口稠密地区空气中放射性沉降物的最高测量浓度”。
不再有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了。在他身上,专业知识、道德和文化权威、在国家中的强大地位曾经紧密结合,化身为科学权威的理想代言人。过去他能够以内部人的身份,公开批判原子试验和军备扩张的问题,警醒和连结公众。但听证会后,他的权力被剥夺了。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记者曾向《奥本海默传》作者之一凯·伯德(Kai Bird)提问: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吗?科学事实是否仍在因为政治利益而被歪曲?
“恐怕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伯德回答。“我们只需回顾一下最近新冠的大流行,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诚信受到公众和政客的质疑,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伯德看来,今天对于科学家的不信任,部分可以追溯到当年奥本海默受到的公开羞辱。这让科学家们对公共政策谨慎发声,无论这些科学知识对普通公民来说多么有必要。如今没有一位科学家享有1945年奥本海默那样的地位,他既是一位公认的科学家,而且公众也愿意倾听他在公共问题上的发言。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奥本海默这样具有科学背景的大公共知识分子了。这是一件奇怪而不幸的事情。”伯德说。
2022年12月,长达68年之后,美国能源部长废除了1954年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为奥本海默平反。也正是这一年,俄乌冲突让告别冷战阴影多年的人们,再一次想起了被核战争支配的恐惧。
现在我们仍然坐在火药堆上。到2023年,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上13,000枚核武器中的大约90%,双方仍在战略导弹和轰炸机上部署约1,500枚热核弹头,准备在下达命令后几分钟内发射。
与此同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每年继续投入数百亿美元来更换和升级其致命武库。由于核军备控制上的停滞,核战争一旦爆发,仅在最初的几小时内可能就会造成数千万人的伤亡。
这也是科学家们的远见所在,没有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人类永远处在毁灭的边缘。正如诺兰在电影结尾警告我们的那样,核战的风险其实从来没有远离我们,最终被点燃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奥本海默传》
【美】凯·伯德【美】马丁·J.舍温 著
汪冰 译
方在庆 审校
中信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本书已在赛先生书店上架,欢迎点击图片购买。
参考文献:
[1]凯·伯德,马丁·J.舍温.(2023).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中信出版集团
[2]Rubinson, P. (2017). Redefining Science: Scientists,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Cold War Americ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3]Rubinson, P. (2018). Rethinking the American antinuclear movement. Routledge.
[4]Wammack, M. D. (2010). Atomic governanc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science in post-war America, 1945-1958.
[5]Thorpe, C. (2002). Disciplining experts: scientific authority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Oppenheimer cas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4), 525-562.
[6]Thorpe, C. (2019). Oppenheimer: The tragic intellec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Diaz-Maurin, F. (2023, August 16). ‘Oppenheimer’, the bomb, and arms control, then and now -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8]Oppie—“A very mysterious and delphic character.” Interview with Kai Bird, co-author of American Prometheus -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23, August 7).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9]The Franck Report - Nuclear Museum. (1946). Nuclear Museum.
[10]Strategic Analysis: The Missed Opportunity to Stop the H-Bomb. (1999).
0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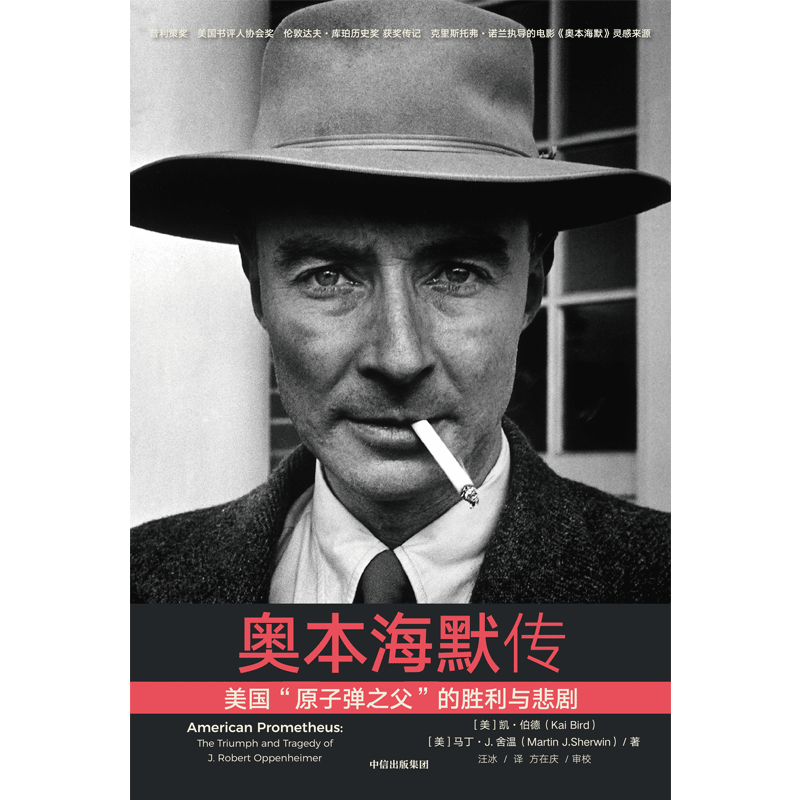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