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叶铭汉(右一)与李政道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方案中的问题。
图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官网
编者按
加速器是了解宇宙奥秘、观察微观粒子世界最重要的大科学装置之一。
早在1953年,美国建成一台能量为33亿电子伏的高能质子加速器时,中国的物理学家们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建成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
但直到35年之后,中国高能加速器项目的历经“七上七下”,才终于在198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正如科学出版社《叶铭汉传》一书所说的,如果1980年不放弃制造质子加速器的方案,真的花费7亿元建造500亿电子伏的质子加速器,建成后将很难进行前沿的物理研究,而且运行费用将很高——按照国际经验,质子加速器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是建造投资的10%,其结果就是中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死亡。
这本书记录了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朱洪元、谢家麟、叶铭汉等几代物理学家们筚路蓝缕,在上个世纪经济、技术和人才及其有限的情况下,为中国的高能物理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来源|《叶铭汉传》
● ● ●
七上七下
1953年,美国建成一台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能量为33亿电子伏,位居世界第一。当时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肖健等对这台加速器十分留意,大家分工做了调研,专门开了一次面向全所的学术报告会,分头报告并进行讨论。尽管当时叶铭汉等正在研制一台700千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能量还不到美国静电加速器的四千分之一,但是我国的物理学家信心十足,坚信中国也会有高能加速器,相信我国一定能赶上,一定会建成中国的高能加速器。
1956年,我国政府决定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当时,我国参加了位于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每年缴纳运行费约1000万美元。在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这一笔钱应该是相当可观的,显示了我国政府对高能物理的重视。
“一上”:1957年,中国派出了一组科技工程人员,在王淦昌领导下,到苏联去学习、进修,设计一台10亿~20亿电子伏的电子同步加速器。这是我国高能加速器的第一次上马。
“二上”:1958年“大跃进”时,部分研究人员也跟着头脑发热,认为10亿~20亿电子伏太低了,应该直接把能量提高到超过当时国际的最高水平,目标改为设计一台15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要争世界第一。
“三上”:1959年,大家认识到,目前我国还没有条件马上建造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所以目标改为设计一台强流的4.5亿电子伏的质子等时性回旋加速器。这是一台中能强流加速器,流强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后来,由于“大跃进”,经济困难,这台加速器不得不下马。
1962年初,我国刚度过困难时期,还有过一次建造高能和低能加速器的讨论,在位于中关村的原子能研究所一部进行,由钱三强所长主持,叶铭汉担任会议秘书,参加者有王淦昌、梅镇岳、赵忠尧、杨澄中、李正武、朱洪元、谢家麟、张文裕等。大家经过讨论,建议建造一台20亿电子伏的电子同步加速器,其指标回到了1957年的指标;另外,建议建造一台串列静电加速器。
这一建议形成后不久因人事和政治形势变化,没有形成正式的文件,无人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记入我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几上几下的历史。
“四上”:1965年我国退出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后,决定在国内建造一台32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当时还考虑过这台加速器要建在“革命圣地”延安。这一加速器的指标是十分落后的,美国在1953年建成的33亿电子伏的加速器于1965年关闭,停止运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一计划又无声无息地自动停止了。
“五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加拿大有人提议建造一台10亿电子伏的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主要用于生产核燃料。原子能研究所一部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原子能研究所二部有人提出建造不同类型的加速器,两个部门分别做了初步设计,双方展开辩论,为此忙了一阵。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后,开始重新讨论高能加速器的方案,这两个方案也就没有人提了。
“六上”:1975年3月,国家批准在十年内,经过预研,建造一台高能质子加速器,这一工程代号为“七五三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任务是预制研究和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第二期工程的任务是研制一台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的高能加速器。这是我国高能加速器计划建造历史上“五上五下”之后的“第六上”。
要实现这一宏大计划,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所有的科研人员人数明显不够。当时高能物理研究所被特批了几十个名额,以便从全国引进工作人员,全所科技人员、工人、管理人员的总数迅速增长,超过100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人员规模最大的研究所。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可以施展才华大干一场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大家认为“七五三工程”的目标不够先进,决定放弃这一计划,这是“六下”。
“七上”:当时,还有一个比“七五三工程”更为激进的方案被提出,这是“七上”。
1977年11月,国家决定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分为三步。第一步:不经过预研,立即建造一台能量级为300亿电子伏的慢脉冲强流质子同步加速器。第二步:1987年底,建成一台4000亿电子伏左右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完成相应实验探测器的建造,建成我国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第三步:20世纪末,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并在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方面做出世界第一流的成果。
这一工程的代号定为“八七工程”,含义是1987年完成4000亿电子伏左右的质子环状加速器。1978年3月,相关人员对方案做了修改,将第一步计划中加速器的能量由300亿电子伏提高到500亿电子伏。
这一决定是非常先进且振奋人心的,叶铭汉当时也十分激动。但现在看来,这一决定却有冒进之失。
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只看到高能物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能物理固然应该发展,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具体条件。首先,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大家没有考虑到当时我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对高能物理的投资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可能占的份额和回报情况。以我国当时的工业和科研水平,我们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一计划吗?假定国家拨付足够的研究经费,我们能按计划完成吗?当时我国 还受到西方的技术封锁,任何器材、方法上的困难都要自己从零开始摸索,独立解决,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能跟上国际第一流水平吗?
当时叶铭汉等科研人员非常乐观,他们坚信,由于我国体制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是这样成功的。可是,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高能物理并没有“两弹一星”那样高级别的优先权,因此目标设定得过于激进。
质子加速器还是正负电子对撞机?
1976年10月初,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所长潘诺夫斯基应邀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
在访问前,潘诺夫斯基和李政道讨论了哪种加速器最适合中国高能物理的起步。当时“七五三工程”是不公开的,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中国已经决定了要建造 3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他们认为,最适合中国建造的加速器是一台质心能量为40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潘诺夫斯基在中国科学院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将轰击固定靶的质子加速器和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性能进行了对比。
他说,从物理实验的角度来看,质子加速器是用高能量的质子轰击固定靶,可以在它的最高能量或较低能量处进行质子打靶实验。也就是说,能量高的质子加速器能做的工作可以完全覆盖能量低的质子加速器能做的工作,能量低的质子加速器就越来越难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领域,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要想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新建的质子加速器能量越高越好,可是建设经费也就相应越来越高。经济上能否负担起这笔高昂的费用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他说,与之相比,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根据要开展研究的物理问题的能区而设计的,在设计选中的比较窄的能区内,该对撞机的亮度最高,偏离这个能量,亮度就会迅速下降。因此,每台对撞机都有它特别合适的工作范围,特别适合于做某一种物理问题的研究。能量高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究领域不能覆盖能量低的电子对撞机的研究领域。即便是国外同行有了能量高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但能量较低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只要选择合适的能区,亮度足够高,依然能生存,还能做出第一流的创新工作。
现在,世界上已有打固定靶的质子加速器,人们还在计划建造能量更高的质子加速器。从物理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要建造新的质子加速器,其能量必须更高,经费也必然更高。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下,这样做是否合适?国外建造加速器的速度可能比中国快,这也是必须考虑的客观现实。
潘诺夫斯基又说,有人赞成建造打固定靶的质子加速器的理由之一是:质子加速器可以产生多种次级粒子,可以做多种实验。他指出,我们应该看一下中国高能物理界的现状。中国现有的做过高能物理实验的科学家屈指可数,即使有了加速器,也不可能有多个实验组同时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因此,质子加速器的这一优点对中国而言并不存在。
总之,从物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能量较低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譬如质心能量为40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有其独特价值,可以做国际领先的基础研究。应特别指出,正负电子对撞机在运行时,同时附带产生同步辐射,同步辐射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光源,在物理学的其他学科研究方面,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当时中国还没有。最后,这样一台对撞机的造价比几十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要低很多,比较适合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
那段时间,叶铭汉主要进行多丝正比室本体的研制,先从小模型做起,再逐步做大,目标是研制成功将来实验用的大型正比多丝室。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原有习惯,一心一意尽最大努力做好。
当前承担的工作,对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什么能量的加速器不太关心,听了潘诺夫斯基的报告,叶铭汉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他讲得非常对,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当时我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七五三工程”,不可能改变了,叶铭汉感到遗憾,认为潘诺夫斯基讲得太晚了。后来他才知道,早在1973年5月中国高能物理考察组访美期间在访问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时,潘诺夫斯基就曾提过建造正负电子加速器的建议。
1977年2月李政道到中国访问时,中国科学院告诉他中国已经有了建造高能质子加速器的初步方案,并开始了预制研究工程。12月,他和吴健雄、袁家骝知道了“八七工程”的内容,三人都不赞同这个质子加速器方案。他们一向尊重中国政府的决定,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但是这次,他们觉得有些意见还是应该反映给高能物理研究所参考,因此三人联名给时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潘诺夫斯基报告的内容。他们的信所表达的是:首先是尊重中国政府做出的决定;如果要问他们的建议,他们倾向于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他们在信中还详细阐述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优点,罗列了可以做的前沿物理研究项目,以及同步辐射的应用。事实上,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最初做的几个实验都在他们的信中有所提及。
但是,因为“七五三工程”已经开始了,不可能改变,所以这封信并没有在所里广泛传阅。叶铭汉等做探测器预制研究的人员仍然专心做手头的工作,他们知道,不管建造哪一类加速器,自己现在研究的探测器技术总是用得上的。
1978年8月,叶铭汉到日本参加第19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会后参观了日本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在该所的招待宴会上,叶铭汉和该所的一位研究员同桌,他的名字是菅原广隆(H.Sugawara)。他问叶铭汉:“为什么要建造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为什么不考虑建 造正负电子加速器?你们计划建造打固定靶的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在物理研究上不是最佳选择。”他又直爽地说:“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一席话令叶铭汉十分惊讶。菅原广隆后来于1989年就任日本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八七工程”下马,高能物理发展受挫
研制高能加速器的计划从1957年开始进行初步设计,到1980年经历了六次下马和七次上马,1980年这一次下马是“七下”。虽然“八七工程”下马,但国家还是十分重视高能物理学,国家已经拨给了高能物理研究所一笔预制经费,当高能加速器下马时,还有余款9000万元没有使用,政府同意将这笔钱用于继续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至于怎样重新拟订高能物理发展的方案,众说纷纭。叶铭汉在美国听到“八七工程”下马的消息,非常失望。至于下一步怎么办,他也一筹莫展。
海内外学者力挽狂澜
彼时,叶铭汉正在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与在西部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访问的中国学者很少联系,也不了解在美国西部的高能物理访问学者的动向。事后叶铭汉才知道,“八七工程”下马后,他们也是议论纷纷,大家感到高能物理前途渺茫。
1980年12月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到美国访问,与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李政道学者”举行了座谈会。钱三强向大家说明了为什么“八七工程”要下马,并鼓舞大家不要灰心丧气,请大家用学到的知识出主意,充分利用有限的财力和人力,尽快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
在钱三强的鼓励下,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访问的中国学者重拾信心。严武光等利用每周中国学者的学术讨论活动,组织大家讨论高能物理下一步怎么办。
李政道在1980年底得知“八七工程”下马的消息,感到十分突然。但他又庆幸,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取消高能物理的发展计划,而是指示“高能物理发展不断线”,并要求中国科学院尽快提出调整方案。李政道十分担心,如果不能及时确定合适的调整方案,中国的高能物理发展又会错过时机,多年的努力将化为流水。因此,李政道决心挽狂澜于既倒。
1980年12月中,李政道到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参加一个会议,他特地挤出时间约严武光讨论了中国高能加速器问题。1981年初,李政道打电话给严武光,说潘诺夫斯基跟他每周至少通话一次,就建造对撞机的可能性进行细致的探讨,希望中国学者也多加考虑。
从1980年12月底开始,李政道一直与潘诺夫斯基联系,讨论适合中国的加速器问题。此时,潘诺夫斯基请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加速器专家伊万·帕特森(Ewan Paterson)做计算,探讨质心能量为40亿电子伏的类似SPEAR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亮度可否做到更高。专家给出一个鼓舞人心的结论——亮度可以比SPEAR高一个量级。
严武光还跟SPEAR上所用谱仪MARKIII的发言人莫兹利(R.F.Mozley)一起查阅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建造SPEAR的有关档案,查明了当初的投资:除人员工资外,SPEAR工程的三大部分——直线加速器、储存环和探测器各投资约1000万美元,总共3000万美元,在当时,正好折合9000万元人民币。这些具体的估算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就现在已有的9000万元人民币,是足以建造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而且其亮度有望超过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SPEAR对撞机的亮度。李政道还认为,高能物理合作是中美两国签署过协议且正在执行中的合作项目,应该继续保持。按计划,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于1981年6月在北京召开,有关中国高能物理发展计划的调整应该及时在会议举行之前提出方案,让有关的代表事先有所考虑。李政道急忙一面打电话给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议派人到美国介绍调整后的方案,一面邀请美国的高能物理专家来华参加讨论。
早在之前,1981年,李政道以私人名义出面邀请美国五大高能物理实验室的专家于3月17日到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参加一个民间的工作研讨会,并邀请中国派人参加,共同探讨在质子同步加速器下马后,中国在新形势下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高能加速器。
中国派朱洪元和谢家麟到美国参加该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通知当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叶铭汉也作为代表参加。美方参加者为李政道、袁家骝、邓昌黎、潘诺夫斯基、威尔逊(Robert R. Wilson,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前所长)、莱德曼(Leon M. Lederman,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所长)、劳(Ronald R. Rau,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副所长)、哈德绍(Walter D. Hartsough,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副所长)等。
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访问的中国学者听到李政道组织研讨会的消息十分高兴,感到有希望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了。大家的意见一致,3月10日,由严武光执笔,15位学者署名,写了一个《关于建造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他们明确建议建造一台质心能量为6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其不仅能提供一个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平台,还可以开展同步辐射应用等为国民经济服务。签名的15位学者是:高树琦、黄涛、王淑琴、郎鹏飞、王运永、黄德强、陈朝清、崔化传、毛振麟、赵国哲、王泰杰、顾维新、黄因智、过雅南、严武光。
在3月17日的工作研讨会上,谢家麟介绍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商定的质子加速器方案之后,大家展开了讨论。在各种建议中,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建造质心能量为44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他估计了建造费用,并列举了可以开展的物理实验项目。他根据他们的一台质心能量为40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SPEAR的建造经验,认为9000万元人民币经费是足够的。经过讨论,与会大多数学者同意这个建议,向中国建议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
早在5年前,即1976年10月潘诺夫斯基来华进行学术访问时,叶铭汉就十分赞同这个想法,在这次会上他当然完全拥护这个更进一步的建议。
朱洪元和谢家麟对潘诺夫斯基的建议进行了非常详细、慎重的研究,觉得建议建造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能量不是很大,规模适中,可以做国际上前沿的物理工作,而且有兼顾同步辐射应用的特点,是我国在当时高能物理科研经费收缩的条件下仍能在高能物理方面 迎头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极好方案。
讨论得出研制北京谱仪的指导方针
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召开的研讨会结束后,潘诺夫斯基邀请朱洪元、谢家麟二人到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访问,并把严武光等写的《关于建造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转交给了朱洪元、谢家麟。
在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朱洪元、谢家麟分别与该所约20位物理学家和加速器专家深入探讨了2×2.2亿电子伏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物理目标与技术问题。这时,中国访问学者得到了向朱洪元、谢家麟反映意见的机会,两位学者和严武光等展开了讨论,李政道也特地从纽约赶来参加。
在讨论的开始,严武光等组织了一系列早已联系好的美国专家的相关报告,然后开始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对对撞机的性能指标比较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最终取得了五点主要共识:第一,探测器原则上采用较成熟的技术,以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探测器之一—在SPEAR上工作的MARK III作为蓝本;第二,加速器采用伊万·帕特森的方案,由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提供资料,制造全部由中国自己完成;第三,电子学器械部分在美国采购集成电路组件,中国自己组装和测试;第四,基于以上三点,中国不需要很长的预制研发阶段,而是按中国现有的条件制造少量的小型样机,成功以后即投入正式的大规模制造;第五,必须及时建立相应的数据处理系统(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这次讨论达成的五点主要共识,后来成为研制北京谱仪的指导方针。
之后,朱洪元、谢家麟还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征求在那里访问的中国学者的意见,绝大部分人的意见是赞同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很少一部分人赞同只建造一台专用的同步辐射加速器,没有人赞成建造质子加速器。
曲折反复的决策过程
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后,朱洪元和谢家麟返回国内,将对撞机方案汇报给领导和有关方面,解释疑问,争取支持。
但是此时国内赞成建造质子加速器的仍然大有人在,朱洪元、谢家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一些人反对建造对撞机的理由是认为以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不足以实现这个方案,谢家麟仔细分析了对撞机的关键技术难点,据理力争,证明我们有能力建成,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
1981年5月初,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与“八七工程”项目组联合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国内很多知名物理学家参加。其后,朱洪元和谢家麟又两次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委会做了方案汇报。一次在北京丰台召开了预制方案讨论会,另一次在河北承德,高能物理学会也对此做了重点讨论。由于对撞机方案具有明显优越性,经过多次汇报、论证与讨论,国内舆论逐渐转向有利于对撞机的方向。1981年7月,高能物理研究所内成立了对撞机筹备组,希望把全所的工作重心转到对撞机的方向上来。这样,对撞机的研制进程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看似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已是板上钉钉了,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时,差一点又回到建造质子加速器的老路。1981年9月,朱洪元、谢家麟和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邓照明三位到美国,为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做准备。出发前,他们接到指示要他们仍然坚持建造质子加速器的方案。到美国后,他们三人向李政道传达了这一指示。李政道十分诧异:这样举棋不定,反复变化,对电子还是质子这个大方向仍不确定,那么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应该怎么开?
李政道以海外学者对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一片赤诚,极力做说服推动工作。邓照明与国内通了电话,经过有关领导再次郑重研究,终于肯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大方向。
1981年10月15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召开了非正式会议,中方正式通报了中国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决定。年底,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向他报告了对撞机的建设情况,邓小平表示这项工程已经定了要干,不再犹豫不决了,应在五年或稍短的时间里建成,经费可以放宽一点,要配备较强的领导班子。从此,中国对撞机的建设真正走上了轨道。
对正负电子对撞机四点质问的回答
1981年,针对选择正负电子对撞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交锋,质疑对撞机方案是否正确,各方面都提出了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对撞机的技术水平很高,国外专家也说对撞机技术困难,你们有把握在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来吗?
第二,现在你们说有物理窗口,但几年之后还有吗?美国SPEAR对撞机会自己不做而把机会留给你们吗?
第三,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费用,国外的估计是不到2000万美元,但中国的国情不同,造价将是多少?如果上马以后,会提出追加费用吗?
第四,中国缺少管理组织大科研工程的经验,能适应这个尖端工程的需要吗?这四个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问的,特别是一直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人,更会提出这些问题。
朱洪元、谢家麟和叶铭汉等对这四个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1977年,丁肇中到高能物理研究所访问,由副所长力一接待,叶铭汉陪同。力一征求丁肇中对中国搞对撞机的看法,丁肇中回答说:“对中国而言,可能太难。”丁肇中的看法和当时很多人的看法相同,而叶铭汉则是赞成选择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人。
叶铭汉本人虽然不是主攻高能加速器方向的学者,但是他做了多年低能加速器,对所内研制环状高能加速器的主要人员大多很熟悉,特别是和徐建铭两人曾一起研制静电加速器。叶铭汉知道他们的工作能力都是很强的,而且他们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在跟高能加速器的设计打交道,并跟踪高能加速器的发展。叶铭汉想,他们如果现在转到对撞机,一定没有太大困难,而且现在加速器设计方面已有一些可靠的软件能直接用于设计。叶铭汉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完成研制高能加速器的任务;在直线加速器方面,谢家麟和他的学们已经建成了一台30兆电子伏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培养了一批人才。因此,叶铭汉深信,我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建成对撞机。
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不仅需要加速器,还需要探测器。高能物理研究所计划建造的探测装置定名为北京谱仪。
有人质疑:“北京谱仪能否与对撞机同时完成?”对于这个问题,叶铭汉也充满信心。他在1979年初第一次参观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实验大厅,虽然之前看过文献,知道它十分庞大,但亲眼看到这个庞大的探测设备时还是感到十分震撼。过了一段时间,他想清楚了:探测器虽然庞大,但本质上也是由一道道小探测器集合起来的。叶铭汉和物理一室的同仁对于其中所包括的各种探测器都相当熟悉,现在要从做几道到做几千几万道,有点儿像工业化生产,就是先制成一个满意的探测器单元,然后大量复制即可。需要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少——有大量复制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问题,有把成千上万道探测单元集合起来时的机械设计问题,有检测上万条信道中每一道的性能问题,有读出每道输出信息的问题,有修理、更换故障部件的问题。但是,叶铭汉知道,这些问题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也可以请海外专家提供帮助。
北京谱仪的硬件研制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探测器本身,通常称为北京谱仪,这一部分由一室负责;另一部分是探测器所用的电子学线路,这部分种类多、数量大,有几万道,主要由席德明领导的六室负责。
一室和六室从1974年起就已经开始做研制高能粒子探测器的准备工作,到1982年时已有8年。这8年中,1974年到1976年因“文化大革命”,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很有限,1977年后研究工作才逐步走上正轨。一室和六室选择了研制电子学类型的探测器,是对撞机上用的探测器。当时我国做了正确的选择,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多数是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到这时已经有了约20年的工作经验。虽然“文化大革命”导致他们有相当多的时间没有用在业务上,但是大家一直很珍惜时光,热爱科学,有空就自学。叶铭汉相信他们都是成熟的有一定水平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完成研制北京谱仪这一重大科学技术任务。
在质心能量为4亿~6亿电子伏能区内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是人所共知的,也就是大家说的所谓“窗口”。但是,知道是一回事,研究是另一回事,必须有合适的实验条件才能进行实验研究。要做实验,就必须先创造条件。在SPEAR上工作的人,早就知道有这些窗口,如果他们能做,那么肯定早已做了。事实上是,他们很想做,但是受到SPEAR对撞机的亮度所限,不能做。谁要做,就必须有亮度高出SPEAR至少四五倍的对撞机才行。换句话说,他们要想把这个窗口关闭,就必须建造一台像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那样能量高且亮度高出SPEAR的对撞机才有可能。全世界高能物理的研究是公开的,建造对撞机的计划也是公开的。建造一台对撞机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建成一般需要七八年。我国现在开始建造,到建成前都不会有别的竞争者。能量高的对撞机不可能降低能量来做我们计划做的工作,因为对撞机的特性是:超出能区范围亮度将大大降低,无法工作。
有人质疑:“质子打固定靶也可以产生陶、粲粒子,因而质子加速器也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提前把‘窗口’关闭。”虽然质子加速器和电子对撞机都能产生陶、粲粒子,但在同一件事上,对撞机有它的优越性,可以在产生陶或粲粒子的阈能附近得到这些粒子,并且本底很小,对于做实验有很大优越性。打固定靶的加速器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不能取代对撞机,不能把窗口关闭。高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产生的粒子中,有的可以衰变为陶、粲粒子,也可以做有关陶、粲粒子的研究,但是毕竟亮度有限,很难跟我们竞争。因此,叶铭汉确信,今后十年内这个物理窗口将一直对我国敞开。
关于建造经费,9000万元人民币够不够?关于经费预算,谢家麟做了极其细致的估算,他认为这笔钱已经足够。事实上,后来1988年11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时,谱仪及电子学仪器共用2940万元,电子直线加速器共用2650万元,储存环及输运线共用3010万元,合计8680万元,可见当时的估价还是十分准确的。
后来按我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的实际需要,增加了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还增强了为全所提供科研服务的计算中心的计算能力。另外,在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同时,进口了一批急需的先进设备,建成了具有国际一流设备的实验室和工厂。这些投资,不属于原来估价的范围。
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同志有一个好传统—绝不做“钓鱼”的预算来蒙骗上级。他们一定精打细算做预算,确实需要多少就提出多少。事实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实际开销和预算十分接近,还略有结余。
我国对大科研工程的管理组织缺少经验,能适应这个尖端工程的需要吗?针对这个问题,叶铭汉认为,管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可以向国外的研究所学习。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能物理研究所人员突然增加,一部分领导来自工业部门,不熟悉科技部门的业务,再加上领导层人数过多(高能物理研究所一度有所长1人,副所长12人),管理上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造成管理效率低下。他认为,只要下决心精简管理系统,并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就可以做好大科研工程的管理。
实际上,后来高能物理研究所在管理上有了很大改进。最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做到了按设计指标、按计划进度、按预算完成,这在国内和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中都是罕见的。
对我国高能物理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
现在叶铭汉回顾我国高能物理发展的“七下八上”经历时,感慨1980年初“八七工程”被迫下马,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次下马,虽然一时间内让国内外高能物理学者灰心丧气,但客观上促使大家重新考虑,放弃了建造质子加速器方案,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李政道以炎黄子孙的赤诚,一心以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己任,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经常回国或通过电话长时间地与谢家麟联系,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上,他坚持正确的方向,耐心做工作,为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洪元和谢家麟以严谨的作风与对高能物理事业的无比热忱,做了大量的宣传、论证工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终于得到我国科学界的认可。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他们两位做出了关键性的重要贡献。
如果1980年不放弃制造质子加速器的方案,真的花费7亿元建造500亿电子伏的质子加速器,建成后将很难进行前沿的物理研究,而且运行费用将很高——按照国际经验,质子加速器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是建造投资的10%,其结果就是中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死亡。花费2.4亿元人民币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使得我国现在在陶、粲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跃居国际领先水平。另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还同时开创了同步辐射的应用,为其他学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手段,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铭汉时常用体育运动作比喻来说明正确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在体育竞技方面,我国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的项目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体操、跳水等,这些运动比较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运动员为国争光,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让中国在国际体坛占有一席之地。我国高能物理的发展过程,正是一个说明选择正确路线的重要性的例子。
《叶铭汉传》
田兆运 陈沫 田茗羽 著
科学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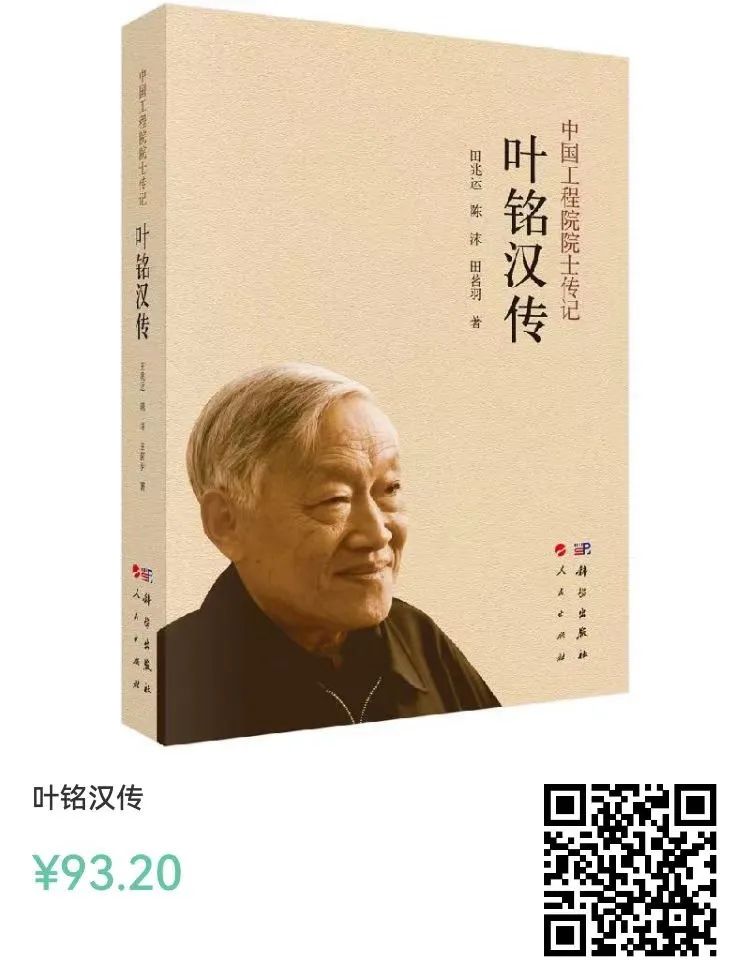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