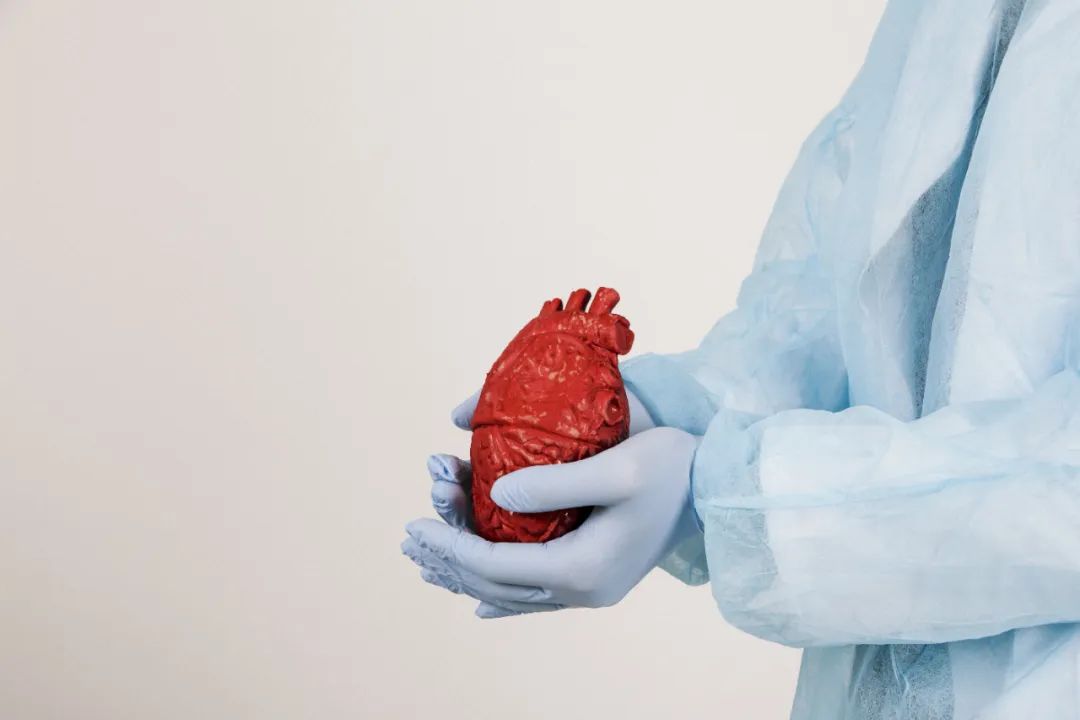
图源:Pixabay
整理撰文丨赵维杰(NSR编辑部)
如果你的某个器官,比如肾脏、心脏或肝脏,几乎完全丧失了功能,而又没有合适的人类器官可供移植,你愿意移植一个猪器官吗?这不是笑话,而是一些医生和研究者正在努力的方向——一个被称为“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领域。
2022年,57岁的心脏病晚期患者David Bennett接受了猪心移植,并在术后存活了两个月。2023年,另一名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Lawrence Faucette在手术后存活了40天。2024年,世界首例猪肾移植的接受者Rick Slayman在手术后两个月左右去世。在这两个月中,Rick曾一度出院,移植团队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他的突然去世是猪肾移植失败的结果。他的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脏病。在中国,2024年报道了一例将猪肝移植到脑死亡患者体内的手术,移植的肝脏在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存活时间超过了10天。
2024年4月,《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组织了一次“异种器官移植”主题的圆桌讨论。这次讨论由赖良学教授主持,其他六位专家参与其中。

赖良学: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关于异种器官移植的讨论。首先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赖良学,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工作。3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动物克隆、转基因大动物和干细胞方面的研究。2002年我在密苏里大学Randall Prather实验室工作期间,和同事们一起培育了世界上第一只杂合Gal基因敲除猪。到目前为止,我的团队已经培育了100多种转基因大动物,包括猪、狗和兔等,在生物医学和农业方面有重要应用。
David KC Cooper:我是David Cooper。我出生在英国,大约40年前移居美国。我接受心脏外科医生的培训,并对心脏移植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我参与了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并在开普敦与全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实施者Christian Barnard教授一起工作了几年。
在美国工作几年之后,我决定放弃临床工作,因为我的主要兴趣变成了异种器官移植。这是因为我意识到人类器官捐赠者的缺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美国4个不同的中心工作过,现在在麻省总医院工作。我们在移植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研究团队,我管理其中一个小组,正在探索在狒狒身上进行猪肾移植。我们还与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小组合作,在狒狒身上进行猪心脏移植研究。
关于猪心脏移植的研究,最早期的应用可能是作为一个临时的“桥梁”用于患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我们可以尝试用猪的心脏来维持婴儿的生命,直到有来自人类死亡者捐献的心脏可供移植,这个等待的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许多婴儿可能会死亡。我们已经在狒狒身上成功地进行了这种桥接式手术。我们乐观地认为,这种方法将在治疗患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方面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我们从“桥接”中获得的经验也将帮助我们最终将猪心脏移植发展为“终极”疗法,即,猪心脏将可以支持患儿的终身生活。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异种器官移植研究,至今已近40年。
赖良学:谢谢。可以说,Cooper教授的职业生涯很好地反映了异种器官移植的历史。
戴一凡:我是戴一凡,目前在南京医科大学工作。大约25年前,我开始在一家名为PPL Therapeutics的公司(现更名为Revivicor公司)从事基因改造和克隆猪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培育出了第一只Gal基因敲除猪,这是基因编辑猪作为异种移植器官来源的一个里程碑。大约在同一时间,赖良学教授的团队也实现了这一重要成果。
这之后我在匹兹堡大学和Cooper博士一起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回到中国,继续致力于猪的基因改造,并将其应用于异种器官移植和其他生物材料或产品的生产。
陈刚:我叫陈刚,现在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工作。早在1998年,我还在读博士期间,就参与了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异种移植研究——我们利用人-DAF转基因猪进行了从猪到猴的异种移植。
在那之后,我去了加拿大,与Robert Zhong博士一起研究从猪到狒狒的异种肾脏移植。然后我回到中国,从事临床和研究工作,主要涉及肾移植。近年来,我与潘登科博士和王怡博士合作,已经进行了20多次从基因工程猪到恒河猴的肾脏移植手术。
潘登科:我是潘登科。我从事克隆猪和转基因工作已经20多年了。2010年,我培育出了中国第一头α-Gal基因敲除猪。我在2018年创立了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已经将α-Gal基因敲除猪培育了十多代,此外,我们还在猪体内引入了10多种不同的基因修饰,用于异种移植。近年来,我们使用6基因修饰的猪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涉及皮肤、肾脏和肝脏等。
张玄: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张玄,是窦科峰教授团队的成员。我们团队于2013年开始异种器官移植研究,首先是肝脏移植,然后扩展到肾脏、心脏和其他猪器官。我们与潘登科博士的公司合作进行猪肝脏异种移植研究,移植后肝脏的存活时间达到26天。我们目前正在脑死亡患者中进行猪肝异种移植研究,并获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
王琳:我是西京医院肝胆外科主任王琳,也是窦科峰教授团队的成员。
我们为什么需要异种器官移植?
赖良学: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异种器官移植?
David KC Cooper:答案相当清楚。这是因为我们无法从已故的人类捐赠者获得足够多的可供移植的器官。在美国,我们每年会进行大约4万例各种器官移植,但却有超过10万名患者在等待移植。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器官来源。
赖良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异种移植的历史。
David KC Cooper: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很多神话中,都有混合了各种动物的形象(例如,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怪物洪巴巴就被描述为公牛、狮子、秃鹰和蛇的混合体)。数千年来,人们一直有将动物物种混合在一起的想法。
但从疾病治疗的角度来看,异种移植真正开始于17世纪,当时人们将某些动物的血液输给人类,通常是将羊血输给有心理问题的病人,因为人们认为羊是非常冷静的动物,它们的血会使病人平静下来。这种治疗可能造成了很多患者的死亡。
这之后,异种器官移植在20世纪初开始,当时的外科医生对免疫反应还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同种器官移植技术发展起来,异种移植就不再流行了。但由于人类器官的短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其他一些人开始考虑使用猪作为可能的器官来源。
第一次相对成功的异种器官移植手术是在1963和1964年进行的。当时,黑猩猩的肾脏被移植到6名人类患者体内。当时可用的免疫抑制疗法非常原始,因此大多数患者只存活了几周,但其中一名患者存活了9个月,并在突然死亡(可能死于急性电解质紊乱)之前回到学校,作为教师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到人类的器官移植并不令人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猪器官移植上。
赖良学:为什么我们关注猪,而不是其他动物?
David KC Cooper:首先,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去使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器官。大多数猴子的器官比我们需要的要小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使用黑猩猩或者大猩猩这样的“大猴子”,但是它们已经是濒危物种,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数量都很少。
此外,饲养非人灵长类动物耗时且昂贵。例如,一只狒狒需要九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成年体型,而且它们每胎只生育一到两个幼崽。而猪可以在几个月内达到成年体型,并且可以大量繁殖。
而且,我们不知道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可能携带哪些微生物。我们对猪携带的微生物相对了解,因为它们已经被圈养了很长时间。而黑猩猩和大猩猩可能携带类似艾滋病毒的东西,这是人们所担心的。
还有,如果我们因为黑猩猩与人类相似、可以为人类提供器官,就开始去屠杀成千上万的黑猩猩,我认为一定会爆发巨大的道德灾难,公众是不会喜欢这种事情的。相比之下,在美国,我们每年宰杀超过1.25亿头猪作为食物,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猪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
除了非人灵长类,与山羊和绵羊等相比,猪也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在室内饲养,不需要去野外,因此更容易与可能传播感染的昆虫隔离开来。
总之,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猪身上,将其作为人类器官的潜在来源,是有充分的逻辑和伦理原因的。
异种移植,适用哪些器官?
赖良学:适合异种移植的器官有哪些?陈刚教授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
陈刚:肾脏和心脏是更适合异种移植的器官,因为在从猪到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的临床前研究中,肾脏移植的效果最好,其次是心脏移植。目前异种肾脏移植后的最长存活时间为758天,在近期的一项异种肾移植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受体都存活了半年以上。异位心脏移植(不移除受体本身的心脏)的最长存活时间记录为近1000天,原位移植(移除受体心脏)的最长存活时间为264天。这也是现有的少数几个异种器官移植临床案例,选择心脏和肾脏移植的原因。
赖良学:肝、肺和其他器官的情况如何?
陈刚:至少目前来看,肝脏异种移植不太可能用于人类患者,因为在临床前研究中,最长的存活时间不到30天。
David KC Cooper:确实如此,但是对异种肝脏移植的需求很大。在早期阶段,猪肝可以作为“桥梁”移植到患者体内,在获得可供移植的人类肝脏,或者患者自己的肝脏恢复功能(这是可能发生的)前,维持患者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需要移植猪肝的存活时间像心脏和肾脏那样长,它能够让患者存活几个星期就足够了。
关于肺,我们的实验结果很差。移植的猪肺很少能在一周之后还有功能。这其中存在一些在心脏和肾脏上看不到的问题,可能与肺的非常精细的结构有关,这些精细结构可能很容易被抗体结合、补体激活或者凝血失调所破坏。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确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事实上,可以用异种移植来治疗的疾病还有很多。例如,美国有3000万糖尿病患者,如果我们能用猪胰岛移植来治愈他们,那就太棒了。欧洲的一个研究小组还将猪的多巴胺生成细胞移植到患有人工诱发的帕金森样疾病的猴子的大脑中,并基本治愈了它们,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
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包括戴一凡,在研究将猪的红细胞输血给灵长类动物。未来,我们将培育出合适的猪作为输血供体,解决人类献血者不足的世界性问题。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决技术问题,所有的猪器官都可能是适合异种移植的。从器官到细胞,异种移植的潜力非常可观。
潘登科:我认为猪皮肤和猪红细胞的异种移植可能会很快进入临床应用。
张玄:正如Cooper教授所说,在短期内,异种肝移植可以作为一种桥接疗法,在患者自身肝功能恢复或同种移植物可用之前,维持患者存活。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是使异种肝移植成为一种终极的疗法。然而肝脏是一个复杂的器官,可以合成500多种蛋白质,而猪和人的蛋白质并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才可能实现完全功能性的异种肝移植。
David KC Cooper:窦科峰博士团队在脑死亡患者身上的研究让我深受鼓舞,猪肝移植物存活了10天以上,这对于肝脏来说是很不错的成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免疫抑制方案
赖良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异种移植中的免疫排斥反应?
David KC Cooper:人体对猪器官的免疫反应比对人器官的反应要强得多。它往往更依赖于抗体结合,而不是细胞排斥。一旦排斥反应开始发展,移植物可以在24至48小时内丧失功能,相比于需要几天才会被破坏的人类移植物来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如何应对。在过去几个月里,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楚,我们可以用补体抑制剂来逆转排斥反应,这种药物可以抑制人类或狒狒的补体对移植物的破坏。我相信这是应对异种移植排斥反应最成功的方法,但是要注意,如果你不尽快开始用药,就会很快失去移植物。
陈刚:如果供体猪没有经过基因改造,异种移植将面临由受体天然抗体介导的严重的排斥反应,导致移植物的迅速失效。但这种“超急性”排斥反应是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预防的,我们可以敲除人类(或灵长类)天然抗体所靶向的猪的主要异种抗原,并引入几种人类的“保护性”基因。
然而异种移植物仍然可能遭受急性或慢性的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这也可能导致移植物失效。因此,除了供体猪的基因编辑外,异种移植的成功还取决于有效的免疫抑制方案。在方案中,包含阻断CD40-CD154共刺激途径的试剂对于预防细胞和抗体介导的排斥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几乎肯定还需要抗凝和补体抑制的方案。
用于异种移植的免疫抑制方案的强度,通常要大于同种移植。因此,受者发生感染并发症的风险就会更大,而这也可能威胁受者的生命。
David KC Cooper:异种移植的免疫抑制方案确实需要比同种移植更强,但是肯定不会强过HLA体液致敏或ABO血型不合患者进行同种移植时所需的方案。我认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免疫抑制方案是相对安全的。
供体猪的基因编辑
赖良学:现在我们来谈谈作为供体的猪。我们应该对供体猪做哪些改造,才能让猪器官在人体内长期存活并正常发挥功能?
戴一凡:目前已有的基因修饰——3个基因敲除以及3到6个转基因的插入——已经涵盖了主要的抗排斥基因。我认为这已经足够好了,不过如果我们想进行更多的基因修饰的话,也许可以添加一些凋亡保护基因,如血红素加氧酶-1(HO-1),或者一些抗T细胞基因,如PD-L1,以防止慢性排斥反应。
在基因敲除方面,最近我们证明猪MHC抗原,也称为猪白细胞抗原(SLA),可以刺激人类T细胞活化并诱导抗SLA抗体的产生,这可能导致异种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因此,也应该考虑敲除SLA,以降低猪器官的免疫原性。
潘登科:还有一点是,转入猪体内的人源“保护性”基因在猪体内的表达水平应该相对较高,特别是人类补体抑制蛋白(如CD55或CD46)和抗凝血因子(如人类血栓调节蛋白)的表达水平,应该与它们在人体内的表达水平相当,甚至更高。我们已经在六基因转基因猪中实现了这些基因的高表达,有助于猪器官的长期存活。
赖良学:到目前为止,我的团队已经改造了超过10个基因,来抑制免疫排斥反应。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非常成功,所以我认为或许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去改造更多的基因。我们可以改造PD-L1、CDLA-4或其他基因,来进一步解决免疫排斥问题。
如果我们要进行更多的改造,可能会导致被改造的猪难以存活。但是我们可以使用条件基因编辑技术,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让这些基因在移植前才开始表达,或者只在特定的组织或器官中表达某些基因,从而让猪得以存活。无菌清洁的环境也有助于猪的生存。
另一个方向是在供体猪体内表达一些人源化蛋白,使猪器官移植到人体后能更好地发挥功能。例如,我们可以在猪肝脏中表达人源化的血清白蛋白,在猪胰腺中表达人源化的胰岛素,或者在猪肾脏中表达人源化的肾素。这样的基因编辑可以帮助移植器官在更长的时间内充分发挥功能。
潘登科: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这个看法。我记得Cooper博士曾经在一次报告中说,更多的基因编辑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David KC Cooper:现有的基因编辑可能已经足够了,继续转入更多基因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这些基因是如何与其他基因相互作用的,或者它们是否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继续添加新基因,最终的效果可能将是有害的,而不再是有益的。我们对此应该小心。
戴一凡:所以我们需要在动物身上测试要转入的基因的功能。但遗憾的是,猴子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动物模型。
David KC Cooper: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基因都进行完整的测试,但或许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测怎样的基因组合可能是必要的且足够的,并测试这些组合的效果。例如,在最近的一例对死者的α-Gal基因敲除猪肾异种移植案例中,手术团队没有给予基于抗CD154单克隆抗体的免疫抑制方案。这个尝试的结果应该可以告诉我们,α-Gal敲除和(或)常规免疫抑制方案是否足以预防排斥反应。
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实践
赖良学:异种移植的临床前研究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潘登科:在中国,获得合适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作为实验受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使用的是恒河猴,它们的抗猪抗体水平比较高,显著高于美国使用的在无特定病原体环境中饲养的狒狒。
陈刚:是的。选择适合试验的受体猴是相当困难的,它们的天然抗体水平通常很高,只有不到10%的猴子能被选中。
David KC Cooper:无论使用哪种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都需要选择那些抗体水平低的个体。中国使用的猴子体内抗体水平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它们的胃肠道中含有能产生大量抗体的特定微生物,而这些抗体也能与猪细胞结合。
我们现在使用的狒狒来自一个特别的饲养设施,它们处于无特定病原体的条件下,因此对猪的抗体水平往往较低。这些狒狒很昂贵,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降低排斥反应的概率。
赖良学:也许中国也需要建设一个特殊的饲养设施。
David KC Cooper:在过去的20到30年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模型对于异种移植领域非常重要。但我认为在当前阶段,和进一步的动物模型研究相比,人类临床试验能够教给我们的东西会更多,这是因为,我们对供体猪的改造是针对人类受体,而不是猴子受体的。猪表达的人类保护基因在狒狒或猴子身上不像在人类身上那么有效。
另一个研究思路是使用脑死亡人类患者作为受体模型。窦科峰博士团队在这方面取得了有价值的进展。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脑死亡模型,因为在脑死亡之后,人体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反应、代谢不相容、代谢不稳定等,这会使这种模型难以把控。尤其是,如果你想要让移植后的器官存活几个月,并在此期间持续记录器官功能,这在脑死亡模型中是很难做到的。
赖良学:在临床尝试中,你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David KC Cooper:病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病人过于虚弱,即便移植成功也很可能不会康复。马里兰州的两名异种心脏移植患者中,有一个人病情严重,就无法从移植中获益。在移植手术前,他就一直在使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已经有几个星期都没能下床。移植到他体内的猪心脏在6周内都功能良好,但即便如此,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只下床活动了一次,因为他实在是太虚弱了。
目前在美国,有许多等待肾移植,但实际上永远都等不到人类供体的患者。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猪器官——而不是向他们隐瞒等待无望的事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别无选择的、真正可能从异种移植中获益的患者。
赖良学:张玄医生,你们是如何说服那位脑死亡受者的家属,同意接受猪器官移植手术的?
张玄:在这个异种肝移植案例中,患者在意外受伤后脑死亡。他的儿子是一名医学研究生,所以当我们向他的家人解释我们的异种移植研究时,他的儿子很快就理解了这项研究的意义,他的家人也决定支持这项手术。他的儿子说,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作为一个对医学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而被人们记住。
关于Cooper教授提到的肾移植,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许多患者因为有酗酒、吸毒等情况,而被排除在等待名单之外,因此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异种移植。但在中国,我们没有类似的限制。所以中国的第一批受者可能会是那些接受过多次肾移植手术、并且不再适合再进行同种移植的患者,或者是已经透析多年、已经难以建立血管通路的患者。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得到补贴并进行异种移植,可能会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猪病毒传染给人?
赖良学:公众对异种移植的一个担忧是,这种手术可能会将动物传染病传播给人类。这种风险确实存在吗?如何预防?
陈刚:我们已经知道,猪巨细胞病毒(CMV)可能引起供体来源的感染。在接受猪器官移植的猴子和两位脑死亡人类患者身上,我们不仅在移植的异种器官中检测到了猪CMV,而且在受者的其他器官,如肝、脾、肺和心脏中,也检测到这种病毒。虽然还不确定猪CMV感染是否会导致受者患病,但我认为,这仍然是一种风险。因此,使用CMV阴性的供体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来治疗这种病毒感染。
戴一凡:在无指定病原体(designated-pathogen-free,DPF)的设施中饲养供体猪,可以清除大多数的猪病毒,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2022年首例异种心脏移植手术的接受者感染了猪CMV,此类事件在今后是可以避免的。
至于猪基因组中含有的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PERV)序列,我们可以通过基因修饰或培育PERV水平很低的猪系来去除它,所以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David KC Cooper:我同意一凡的观点。关于PERV,我们无法通过将猪饲养在清洁的环境中来消除它,但是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会像CMV那样导致移植失败。我认为是否需要去除PERV序列,应该是监管机构要去决定的问题。目前,美国的监管机构似乎并不认为供体猪必须不含PERV序列。
事实上,来自清洁设施的猪会比人类捐赠者“更干净”,所以我不认为异种移植带来的感染会比同种移植的更严重。真正的挑战仍然是免疫排斥反应。
潘登科:在中国,中科奥格在2022年建立了第一个DPF设施,并已经获得了第一代无病毒猪。大多数病毒和细菌都可以被清除。此外,我也同意PERV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敲除它。
戴一凡:关于病毒的问题,样本监测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FDA要求研究人员将猪的组织和血液样本在冰箱中保存至少50年,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回过头去检查,找到那些可能存在的“未知”病原体。
伦理问题
赖良学:异种器官移植会打破人和猪之间的物种界限吗?这是很多普通人可能会问的问题。
David KC Cooper:我认为,如果我们遵循两个原则,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第一,我们不应该改造猪或人的大脑与思维过程;第二,我们不应该改造猪或人的生殖系统,这样他们就不会生出带有猪基因的小孩或带有人类基因的小猪。
遵循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一个人体内有一个猪器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他体内的猪器官也就随时死亡了。所以我不认为物种之间的界限会被打破,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陈刚:我们可能需要密切观察接受了异种移植的患者,并对他们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对生育的限制,以防止在下一代身上发生意外的变化。
赖良学:所以这个问题是:接受猪器官移植的人是否可以结婚生子?大家怎么看?
戴一凡:我认为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做。
潘登科:我也是。我在转基因猪领域工作了很多年,我认为猪基因转移到人体内并遗传给下一代的机会微乎其微。
David KC Cooper: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考虑接受猪器官移植者的心理问题。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担心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对孩子们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小孩子很可能会对其他孩子很不友善。如果他们知道有一个小孩儿有一颗猪心,很可能会嘲笑他、欺负他。
赖良学:确实如此。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与公众沟通?
戴一凡:每一次异种移植的新闻出现在媒体上,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公众的机会。在我的观察中,公众对异种移植的态度是肯定多于否定的。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教育他们的机会。
David KC Cooper:非常正确。我在阿拉巴马州工作时,我们曾经对病人和家属进行了一些调查。结果很明显,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异种移植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们询问那些等待心脏移植的婴儿的母亲,她们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换一颗猪心的时候,她们通常会说:“如果这能让孩子活下去,是的,我愿意。”当我们告诉他们,这些猪是经过基因改造的,他们通常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会觉得普通的猪是一种相当肮脏的动物,但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猪要好得多。
所以,虽然公众对异种移植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教育,他们会习惯这种想法的。事实上,在50到60年前,人们对同种器官移植的态度就发生过这样的变化。最初人们完全不理解器官移植,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很好地接受了同种器官移植。
王琳:除了与公众的沟通,与管理部门的沟通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问题。以我们的脑死亡患者手术为例,要让医院、学校和空军的领导理解和接受这项研究很不容易。他们的主要担忧之一是,公众是否会接受异种移植的概念。转折点出现在,《自然》杂志采访了我们,并发布了一篇这一主题的新闻报道。领导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才开始接受我们的实验。因此,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要让公众接受异种移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潘登科: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与内江市的政府部门有过很多交流。起初,他们都不理解异种移植,认为这就是一个笑话。但在五年之后,他们现在已经非常热情地支持我们的工作。Cooper博士曾经提醒我说,我们应该多写文章,并积极与地方和国家官员沟通,及时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新想法。这些做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未来:异种移植取代同种移植?
赖良学:这个领域在5到10年内会有怎样的进展?20年或50年之后又会怎样?
David KC Cooper: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将会培育出“完美”的供体猪,让我们在进行异种移植器官时完全不需要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它们的器官会通过基因工程来保护自己。这对患者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免疫抑制,也不再容易受到感染——或者至少风险会小得多。
从长远来看,也许在50年内,我相信人们将不再需要由死者捐献的器官,因为猪将提供比人类更好、更干净、更少感染的器官。同种移植最终将走进历史。也许再过50年,人们会坐在一起说:“你知道吗,从前人们会移植死人的器官。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异种移植将成为唯一的移植形式——除非有干细胞培育器官等其他技术可以取代猪器官移植。
陈刚:我认为在未来,异种移植可能会与同种移植长期共存,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异种移植,但它不太可能完全取代同种移植。
王琳:在我们最近的手术之后,有一位类器官研究者对我说,她认为异种器官移植是比她所研究的类器官更好的治疗方案。因此我相信,异种移植很可能是该领域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
根据我们团队的计划,今年内我们希望把猪的完整肝脏移植到一位脑死亡患者身上。在明年或者其他时候,我们还希望在生存的肝脏疾病患者身上进行猪肝脏移植手术。
潘登科:人们经常会问猪器官移植何时才能成为常规的临床操作。Cooper博士,你怎么看?
David KC Cooper:我认为在美国已经很快了。我们正在做一两个临床案例,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些案例是相对成功的,监管机构很可能会对此持相当积极的态度。我的感觉是,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异种移植将会进入临床,并且对此不再有重大保留意见。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向他们证明我们可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赖良学:谢谢。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除了猪器官移植,还会有其他的技术选择吗?比如,我们能在猪身上培育出人器官吗?
实际上,我的团队已经在猪体内的人源化器官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我们使用人类干细胞来培养人-猪嵌合胚胎,已经在猪体内获得了发育约28天的人源中期肾脏。这是非常初步的工作,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猪身上培育出成熟和有功能的人体器官。人的妊娠期约为10个月,而猪的约为4个月,如何协调器官发育的节奏是一大挑战。我认为也许在5到10年内,我们可以从供体细胞和受体猪身上都做一些改造,从而实现器官的同步发育,在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好的结果。
戴一凡:赖老师团队在人源化器官方面的工作很有前景。我认为这两种方案可以并行发展,我们一方面继续对猪器官进行改造,也同时进行人源化器官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一些难以进行异种移植的器官,比如肝和肺,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人源化的肝和肺,对患者来说会是非常好的消息。当然也许我们应该从“简单”的器官开始尝试,比如肾脏。
潘登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源化的器官还是嵌合的,仍然含有猪细胞,因为我们很难在猪体内获得100%人源化的器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仍然需要使用低免疫原性的转基因猪来培育人源化器官,从而将免疫排斥反应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赖良学:我认为我们可以结合这两种技术来解决免疫排斥问题。将人类细胞添加到猪器官中,或许能够解决一些无法直接通过对猪进行基因改造来解决的问题。我希望这两个方向的研究人员能够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David KC Cooper:如果有时间和资金,我们当然应该探索所有这些方法。但我认为,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我们将能够培育出不会在人体内引发免疫反应的猪器官,或者至少,我们能够保护移植物不受免疫反应的影响。如果这种“通用供体”成为现实,那么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太可能比它更成功。所以,只要专注于猪的基因工程,我们就可以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但我真的相信这是可能的。
*本文是NSR Forum文章“Pig Organs in Humans: a Forum on Xenotransplantation”的中文版本,英文原文链接: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