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撰文|钱岳
追问工作的意义
最近微博上有一个热搜:“35岁你会发现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在超长工作时间、生活压力大的社会,关于工作意义的讨论,直击每个人的内心。学术界的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天职、是calling,似乎和有关“意义”的讨论不搭边。但是,拿到终身教职之后,我一边按部就班地干本职工作(做研究、教课等),同时也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读博士时,目标是博士毕业、找到教职(如果地理位置能好一点,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入职助理教授的岗位,目标是拿到终身教职。所以,从2010年开始读博士到2021年拿到终身教职,在这11年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埋头赶路的紧迫感,反而让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纠结“为什么”的问题。
拿到终身教职后,我就在想: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虽然通过研究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常常满足了我想了解社会的好奇心,但不得不承认,写作以及学术工作也伴随着压力和自我否定。是否有满足探索欲之外的其他目标,让我可以无畏艰辛地充满干劲地继续前行?我仔细想了几条“显而易见”的答案,但都不能让我满意。比如:
成为正教授?这在我看来不算目标,因为只要我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晋升正教授似乎是以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争取学术头衔?但我对学术界的title(头衔)以及status(地位)的追逐,兴趣不大。有朋友建议我申请一个Canada Research Chair(加拿大政府设立的首席研究员),但我始终找不到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充分回答“为什么申请”的理由。
拿大笔的研究经费?之前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拿到终身教职,我积极地写基金申请,也成功拿到了一些国家级的项目。2018年,我第一次成功申请到国家级的项目基金后,同事在家里办了一个派对替我庆祝。她开玩笑地说:“Yue,这是我为你办的第一个‘基金申请成功派对’,也会是最后一个类似的派对,因为你以后就会发现,拿到研究经费不过是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我这几年越来越意识到,同事作为过来人,她说得太对了。我的研究主要以分析现有的大型数据为主,所以要做高质量的研究,除了花时间之外,对于项目经费的要求并没有特别大。但是,在加拿大,研究经费一般不能用来“买时间”(比如,把经费给系里用来聘请其他人代替我教课),所以拿到研究经费,无形中等于承受更大的压力把教课之余的时间花在新申到的项目上。经费越多、项目越多、工作越多。
继续发论文?这不能算是目标,只是我工作按部就班的一部分。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回答“为什么发论文”的问题。有朋友跟我说,“we never heard a dying person say, ‘I wish I’d publish more papers’ ”(“我们从未听说过一个垂死之人说:我希望我能发表更多论文”)。所以,在接下来至少30年的学术生涯中,紧盯着“发论文”这件事,似乎也不能激发我的内在动力。
我还跟心理咨询师探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我从小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教育环境下长大,所以我一直处于survival mode(求生模式)。就仿佛我没目标、不努力,就会考不了高分、上不了好大学、毕不了业、发不了论文、拿不到教职、失去工作……所以,我从7岁到35岁之前的生活,都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求生和打怪升级模式。从小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再加上后来在北美作为少数族裔,我已经内化了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我习惯性地认为,我需要用事实证明我的能力,才能获得外界的认可,而且别人可能会低估我的能力,所以我需要表现得比预期要“更快、更高、更强”,才能顺利闯关。她说,“但是你现在已经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了。你有很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你不需要强迫自己生活在求生模式中了。你是安全的。Relax(放松)。”
道理听起来容易,执行起来难。后来,我问自己:过去的这些年里,你真正觉得快乐的时刻是哪些?忠于内心的快乐,而不是被外界对于“成功”的评判标准所左右的快乐。在赶路的时候,学会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或许是我找到内在动力的第一步。
认清对我重要的事情
过去这几年,我干劲最足的时候,或许是疫情期间我做关于武汉的研究的那段时间。当时疫情刚刚爆发,我看到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鼓励研究者申请经费做疫情相关的研究。作为从小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人,我当时心情特别焦虑,觉得自己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做研究了解疫情对自己家乡人民的影响。当时两个星期,我跟合作者一起写了一个很ambitious的项目基金申请,那两周我几乎不眠不休,每天就是在改研究计划书。最后交上去的时候,我感觉研究计划书不仅包含了我的学术理想,还有我的真情实感和强烈的“一定要做成这件事”的意念。后来,如愿以偿拿到基金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激动,因为即将要做的研究,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it means a lot to me personally)。
后来,做这个武汉研究成为我在疫情时的寄托,每天睁眼就起床工作,一工作就不知不觉是长长的一整天。做研究的过程,帮我消解了非常多疫情期间各种不确定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国斌老师在他的学术专著《The Wuhan Lockdown》的前言里写,“when we were unable to go out as we used to, I could at least devote my time to writing.”当时读到这里,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切身体会,是研究、写作和工作给我带来了巨大慰藉。(写到这里,我也需要反思我的privilege,我没有家庭照料的责任,所以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中,这是需要照料家中小孩、老人、病人的学者所没有的自由。)
我和合作者通过这个项目发表的几篇论文成为我自己最珍视的一些作品。这些论文不全在我长期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内,我也不一定把它们列在晋升需要提交的“代表作清单”里,但是写这些论文给我带来的意义感,以及最后呈现的作品,都是“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最无愧于心的答案。

因此,拿到终身教职之后,鼓励自己慢慢走出“求生模式”,从事让自己觉得(智识上、情感上)激动和重要的研究,或许可以是我工作的内在动力。(我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能够找到这样的项目本身就是莫大的幸运,如何能够持续地发掘这样让自己无比激动的项目,也是我还在思索的问题。)
建立人与人的联结
我最近听了特别多有关“生命的意义”的podcast,感觉总结下来,心理学研究发现,建立人与人的联结能让人感到生命的意义。我仔细回忆,这几年哪些时刻是让我觉得真正快乐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芝加哥大学的边琳老师分享过的一个感悟:“和一个朋友…吃饭间也吐槽学术圈的不容易,每发一篇文章从设计实验到数据分析到写文章再到修改都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一个细节也会反反复复琢磨很久,朋友问精益求精真的有意义吗?我答:有吧,起码对得起自己。”这种对精益求精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而如果一起工作的人跟你志同道合、有同样的追求,那么意义感就好像翻倍了,也更鼓舞人了。
网上很多人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去搭一个不草台的班子,然后一起做1+1>2的事情。这种一边创作自己满意的作品、一边还与自己合得来的人保持定期联系,真是不可多得的福利。我前段时间改论文还发过下面这个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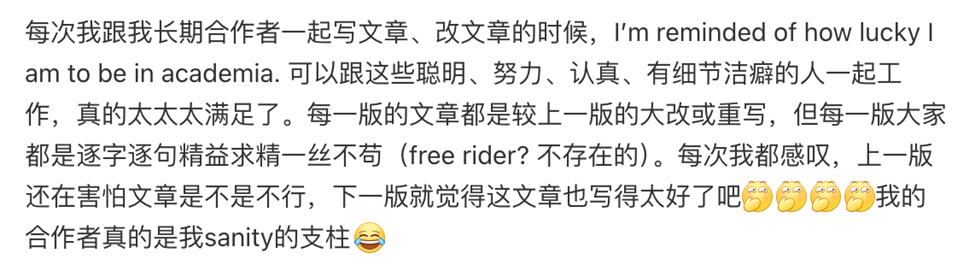
遇到问题想不通,就好像玩拼图时有个地方怎么也拼不上,不解决的话,有些人可能吃饭睡觉都不安稳。自己找答案,有时候容易钻牛角尖。幸运的是,我遇到的合作者,他们非常耐心地听我描述问题和困惑,然后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并且帮我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研究中的波折……每次经历这样的时刻,我都发自内心地感恩,能够建立这样人与人的联结,找到一起不厌其烦地解决问题、精益求精地完善作品的同伴,何其所幸。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不擅长留于表面的寒暄,但是非常珍惜深层次的交流(deep conversations)。很多时候,合作者也是密友,大家除了一起做学术,如果在职业生涯或个人生活遇到问题,也会互相交流、打气、找到面对人生困境的底气。所以,建立持久的学术合作和更长久的超越学术的友谊,同样是激励我工作的意义和内在动力。
真诚友好的人与人的联结,不一定是建立在合作者之间的,它也可以是mentor(辅导)学生带来的联结,或者在做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有社会意义的工作时,与其他群体建立的联结。我常常因为追问工作的意义而觉得庸人自扰,但是工作中建立的实实在在的积极温暖的人际关系,总能提醒我要珍惜这些“小确幸”。
结语
我写的《一周年系列|在加拿大当助理教授的第一年:如何管理时间、情绪和研究进度?》这篇文章,更多是分享我摸索出来的提高productivity(工作效率)的方法。但是,写完这篇post-tenure的文章,我才发现,我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tips可以提供。在学术界拿到终身教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学术也是一场马拉松,如何在每天和长期的工作中,让自己觉得有意义,不负于心、不负于时间,是一个比提高工作效率更难回答的问题。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