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O. 威尔逊(1929年6月10日-2021年12月26日)
编者按
据多个媒体报道,哈佛大学教授E.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于美国东部时间12月26日下午去世,享年92岁。威尔逊是一位极富影响力的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他发现了400多种蚂蚁,以在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著称,被誉为“当代达尔文”。威尔逊也是一位高产的科普作家,撰写了30多本书,其作品曾两次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并普及了 “生物多样性” 一词。正如威尔逊的同事、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家Hopi Hoekstra所言,“人们会非常想念他”。今天,《知识分子》推荐古生物学家苗德岁眼中的威尔逊以及对于他极富争议的《社会生物学》一书的评论,了解这位影响世界的科学家的重要学术贡献。
撰文 | 苗德岁
在当今生物学家中,哈佛大学退休教授E. O. 威尔逊,被称为是达尔文的传人,甚至有人称其为 “当代的达尔文”。本文谈谈威尔逊为捍卫达尔文学说,曾受过的一段不公正对待。
威尔逊1929年生于美国的亚拉巴马州,从小就酷爱博物学,立志长大以后成为鸟类学家。他不幸在一次钓鱼事故中右眼受伤变残,考虑到一只眼会严重影响野外观察鸟类活动的效果,便决定改学昆虫学。这样的话,尽管只有左眼一只好眼,但在显微镜下观察昆虫形态,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即被留校聘为助理教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蚁类的社会行为的,不久他便成为全世界这一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
威尔逊暴得大名是因为他的《社会生物学》一书。该书197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名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是一本厚达700页的大书。这本书的问世,不仅标志着社会生物学这门崭新学科的诞生,还引发了一场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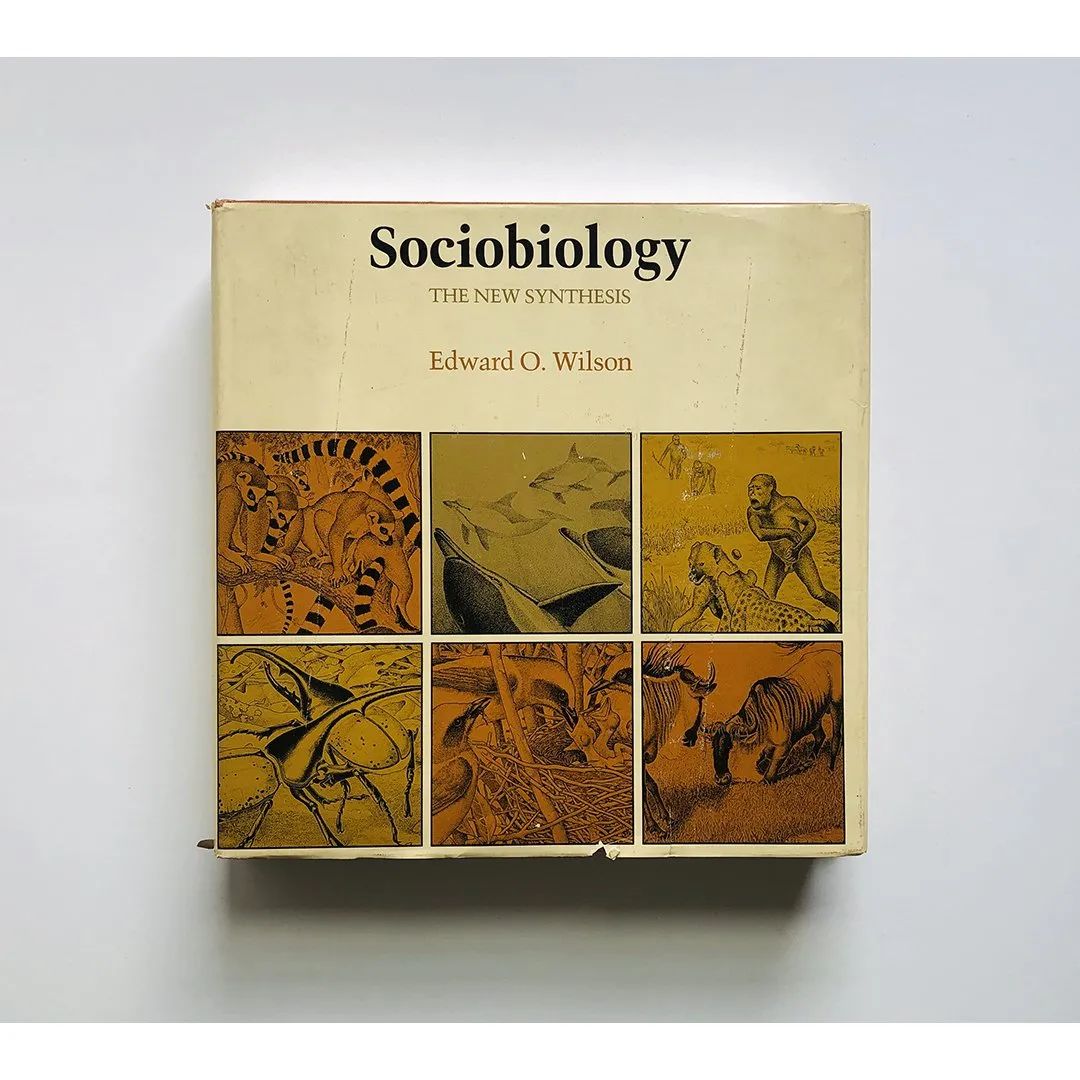
图1 《社会生物学》
作者在书中用大量动物行为研究的例子,从遗传学、种群生物学、生态学等方面,系统地描述了生物中各种社会行为(如性行为、侵略行为、互惠行为以及亲子抚育等)的表现、起源和演化,并借此论述了社会生物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该书的前26章,介绍了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从蚂蚁到大象,无所不包)的社会行为,说明这些社会行为都是为了使生物所携带的基因更容易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因此是符合达尔文学说的。当然,这部分内容很少引起什么争议。事实上,书中反映出威尔逊的渊博学识和治学严谨,使他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仰慕。
争论主要源自该书的最后一章(即第27章 “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在该章中威尔逊把社会生物学应用到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上去。因此,他认为,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包括侵略性、自私性,甚至于性爱、道德伦理和宗教等),都是因为对物种的生存有益,因此通过自然选择筛选、保留而演化出来的,这跟其他生物没有什么不同。万没想到,这下子他竟捅了个大马蜂窝!
顿时,威尔逊的观点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强烈反对。批评者称威尔逊为新斯宾塞学派的代表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对于威尔逊的批评,很快地超出了学术范畴,而且很快地发展成了人身攻击。而攻击他最厉害的人却是他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两位哈佛大学同事。这两位的名字在生物学界也是如雷贯耳:遗传学家理查德·莱万廷与古生物学家古尔德。
按说他们三人在同一个办公楼里上班、在同一个系里共事,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完全可以面对面地讨论——哪怕是争吵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令威尔逊不解(也使他非常寒心)的是,理查德·莱万廷与古尔德背着他,连同另外15个人共同署名,在1975年11月13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目为 “反对《社会生物学》”。
理查德·莱万廷是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大牛,而古尔德不仅是古生物学界的牛人,而且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因此,由这两位参加署名给《纽约书评》写的公开信,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就非同一般了。公开信中明确指出:“从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以来,生物和遗传信息曾在社会和政治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从斯宾塞的 ‘适者生存’ 到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都宣称自然选择在决定大部分人类行为特性上起着首要作用。这些理论导致了一种错误的‘生物(或遗传)决定论’,即生物遗传决定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因此给这些行为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同时,这种 ‘生物(遗传)决定论’ 还认为,遗传数据能够解释特定社会问题的起源。”
公开信中还进一步指责威尔逊有种族和阶级偏见,说他在为维护资产阶级、白人种族以及男性的特权寻找遗传上的正当性。由于威尔逊出生于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州,该州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曾站在维护黑奴制度的一方,而威尔逊又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男性白种人,因此这无疑是在指责威尔逊是种族主义者,并说《社会生物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卷土重来的信号。这一下子深深地激怒了威尔逊,使他不得不自卫反击。
被包围在批判声中的威尔逊再也不能忍受别人(尤其是自己的同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了,于是他在1975年12月11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反驳信。他在信中指出,他的批评者不仅歪曲了《社会生物学》及他本人的科学用意,而且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这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精神。
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那封公开信的签名者中有两位是跟他在同一座楼办公的同事(指理查德·莱万廷和古尔德),而他居然是在那一期《纽约书评》上了报摊之后才看到公开信的。试问究竟是谁在背后搞阴谋呢?
威尔逊之所以反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公开信中曾指责《社会生物学》是宣传美国右翼的政治观点,而且影射威尔逊参与了右翼的阴谋活动。
威尔逊的反问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理查德·莱万廷和古尔德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中,都曾是活跃分子。
由于理查德·莱万廷和古尔德两人都是犹太人后裔,对希特勒的种族清洗(屠杀犹太人)有切肤之痛,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敏感。尽管从这一角度上说,他们对《社会生物学》的问世反应异常强烈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平心而论,这场论战也确实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存在左右两派这一事实;理查德·莱万廷和古尔德都曾公开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正当美国的这场关于 “社会生物学” 的论战方兴未艾的时候,1976年(即《社会生物学》问世的第二年)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牛津大学一位年轻的动物学讲师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道金斯在书中主要想把演化生物学研究(尤其是对自私和利他行为的研究)的新进展介绍给行外的人。其中的内容涉及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些生物学家以及他们提出的各种理论。他书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接近威尔逊的观点,但也有些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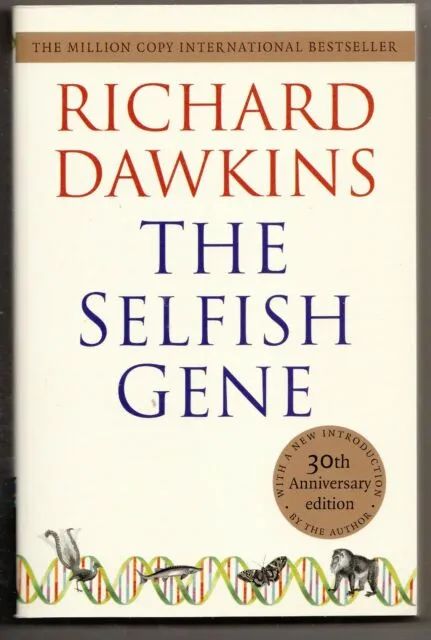
图2 《自私的基因》
首先,他引进了两个新概念,一是把生物体称作 “运载器”,二是把基因称为 “复制品”。依照他的观点,只有基因才是不朽的,每个生物体只是基因的载体,基因可以通过复制,从一个载体传到另一个载体,历经无数世代。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体只是一个暂时的运载器,其作用是负责把复制基因传给未来的世代。因此,自然选择是在基因水平上起作用的,而不是上面提到的 “个体选择”,更不是 “群体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道金斯比威尔逊更激进。
因此,古尔德把道金斯的自私基因论称为 “极端达尔文主义”,也有人因此称道金斯为 “达尔文的罗威纳犬”。还记得赫胥黎的外号叫 “达尔文的斗犬” 吗?罗威纳犬可比斗犬更凶哦!
《自私的基因》是一本科普书,对外行来说,比《社会生物学》更容易理解,因而在公众中的影响也更大。道金斯的出现,无疑给这场大论战 “火上浇油”;事实上,在后来的持久战中,古尔德基本上是找道金斯 “单挑”!他俩都是一流的科普作家、写文章的高手,两人笔战起来,也格外好看。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威尔逊啥事了。
恰恰相反,1978年2月13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威尔逊走上讲台正要做报告时,突然冲上来一位女子,将手中的满满一杯水浇到威尔逊的头上,台下则有一帮学生为她助威,不停地齐声高喊:“威尔逊,你全错了!” “威尔逊,你全错了!”
有意思的是,“威尔逊,你全错了!”在英语的习语中是:“Wilson, you’re all wet”;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直译的话则是:“威尔逊,你湿透了!” 在这场 “闹剧” 的全过程中,威尔逊从未失态。他擦干了脸上的水,继续做完学术报告。
凡是了解威尔逊的同事们都知道,威尔逊是一位典型的绅士、顶尖的学者,他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更不是什么坏人。这就像达尔文一直被有些人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一样,尽管达尔文祖孙三代都是反对蓄奴制和种族主义的。
尽管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饱受争议,但是,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从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荣获美国总统卡特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也曾荣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克拉福奖(因为诺贝尔奖未设生物学奖,故该奖实际上相当于生物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他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 “全美最有影响力的25人” 之一。
“老树春深更著花” 是顾炎武的名句,现在一般用来赞美人到暮年,雄风犹在、壮心不已。在我心目中,E. O. 威尔逊是学术界最不负 “老树更著花” 这一美誉的。他虽已至耄耋之年,自1996年从哈佛大学教职上退休以来,老当益壮、勤勉著述、新作迭出,于今已出版了16本书。他的新著《创世记:社会的深层起源》,即是他退而不休后的第16本书(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第32本书)。“著作等身” 这一成语用在威尔逊先生身上,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实情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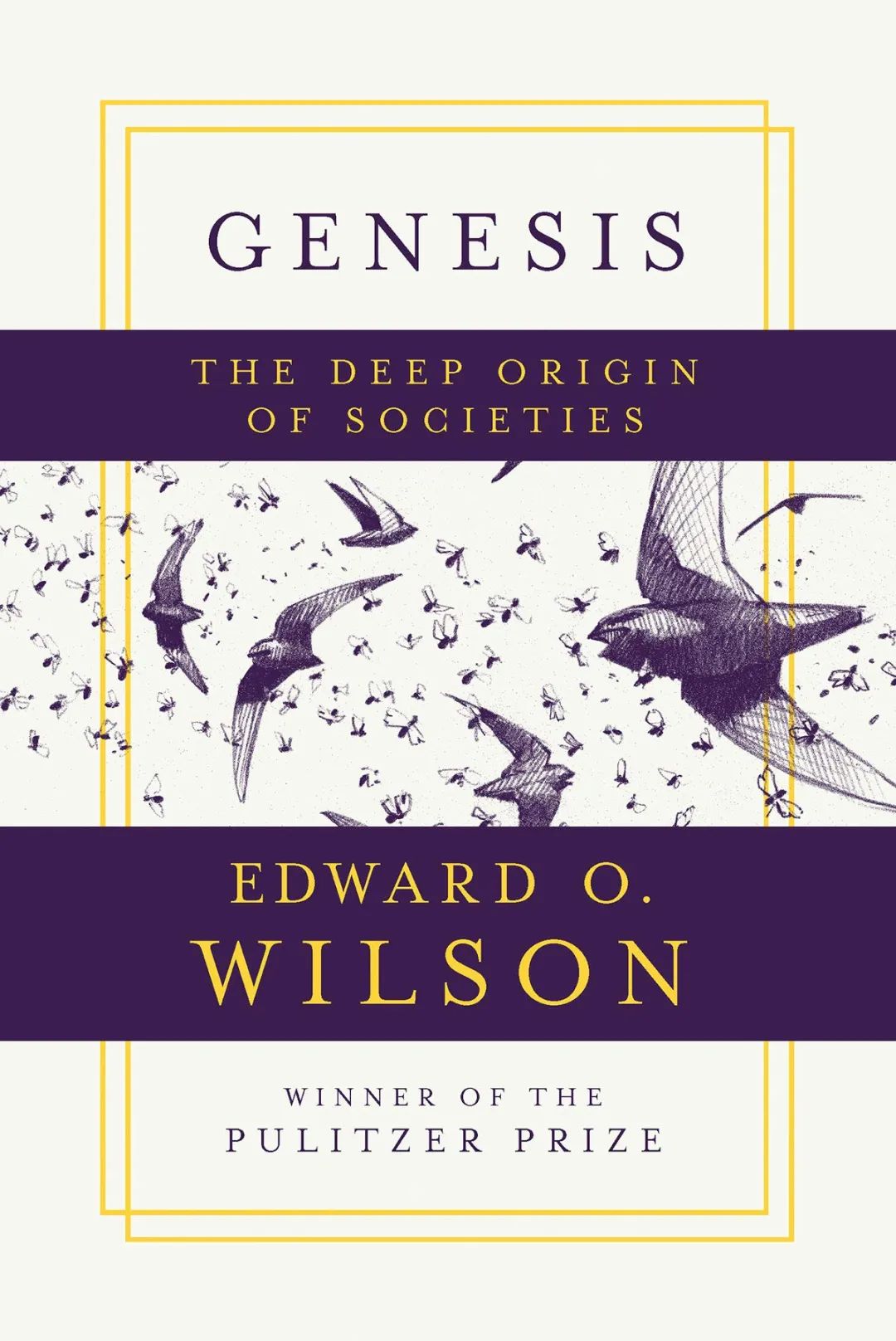
图3 《创世纪》英文版
比起他之前的很多洋洋大观之作,这本新书只是不到150页的 “小书”;而这种 “大家小书”,又恰恰是他在一生丰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充满深度哲思的 “大书”。在本书中,威尔逊先生回到了他的成名作《社会生物学》的主题,进一步探讨我们生而为人不免常常思考的问题:究竟何以为人?在亿万年来地球上所有生存过的众多物种中,为什么唯独我们达到了“万物之灵”的智力高度,并形成了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对此,他毫不畏惧地表达了他一贯的达尔文主义科学思想与综合理论:所有的宗教信条与哲学问题,皆可解构为纯粹的遗传与演化组件;人类的肉体与灵魂均有其物质基础,因而完全遵从宇宙间的物理和化学定律,绝不是超自然的。因此,若想充分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的深层起源,我们还必须深入研究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的演化历史。
鉴于此,威尔逊先生在本书 “引言” 中写道,“事关人类处境的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第三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与未来。然而,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两个问题有准确的把握。总体而言,对于前两个涉及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出现之前更久远的历史的问题,哲学家们缺少确凿可证的回答,于是,他们也无力回答事关人类未来的第三个问题。”坦率地说,我尤其认同这段话,因为长期以来,我对哲学能够指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这一 “神话”,一向持怀疑态度。
威尔逊先生还指出,长期以来,对人类的由来及其存在的意义,解释权都为宗教组织所掌控。地球上有4000多种宗教幻想,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带来了纷繁的部落意识,而部落意识又正是 “人类的起源方式带来的一个结果”。
直到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开始把物种起源(尤其是人类起源)的 “整个主题带进了科学探索的视野,并提出了人类是非洲猿类的后裔”。实践证明,达尔文是人类观念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他的生物演化论对旧观念的颠覆是 “石破天惊” 的。此后,神学家们赖以支撑门户的《创世记》便难以自圆其说。诉诸神灵来解释世上万物的由来、我们何以为人以及如何行事等 “自我认知” 问题,不再令人信服。此外,一百多年来,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这五个领域里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使 “我们具备了相当充分的知识来回答人类的起源问题,包括起源的时间和方式”。正是这些科学进展,促使威尔逊先生信心十足地撰写了这本“科学的创世记”,向大家讲述无比精彩的、真正的人类起源故事。
本书的前半部包括三章,分别是:1.寻找创世记,2.演化史上的大转变,3.大转变的两难问题及其解决之道。首先,威尔逊先生 “粗线条” 地大笔勾勒了生物演化的宏观图景,带领我们重温了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达尔文理论,以及基因突变、环境筛选、表型可塑性演化等新达尔文主义(又称作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相结合的“现代综合系统学”)核心概念。他强调指出,“科学家认为,演化不只是一个理论,更是一个已被确证的事实。通过野外观察与实验,科学家已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然选择作用于随机突变,正是演化实现的方式”。
接下来,他追踪了长达几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其如椽大笔一挥,浓墨重彩、举重若轻,令人叹为观止:“地球生物历史始于生命自发形成的那一刻。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生命先形成细胞,再形成器官,又形成组织,最后,在过去两三百万年里,生命终于创造出了有能力理解生命史的生物。人类,具备了可无限拓展的语言与抽象思维能力,得以想象出生命起源的各个步骤—— ‘演化史上的大转变’。”
他进而指出,这些“大转变”依次为:1.生命的起源;2.复杂(真核)细胞的出现;3.有性繁殖的出现,由此产生了DNA交换与物种倍增的一套受控系统;4.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5.社会的起源;6.语言的起源。有趣的是,为什么是 “6” 而不是另一个数字?同以人类为视角,为什么 “脊索的出现” “颌的出现” “脊椎动物登陆” “羊膜卵的出现”,抑或 “人类的起源” 等,不能算作同等重要的 “大转变” 呢?这不禁让我想起布封在划分地球历史的自然分期时,也是用了 “6” 这个数字,恰恰与神学《创世记》中上帝用6天创造了世上万物不谋而合。或许,“6” 这个神奇的数字真是 “天生”(hard-wired)地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在中国文化中,“6” 则象征顺遂、幸运)。
值得指出的是,威尔逊先生对生命大历史的描述,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妙趣横生:“于是,没有任何确切目的,仅仅凭借着变幻无常的突变与自然选择前行,在爬行动物时代就出现了的导向系统的引领下,经过三十八亿年,这副包裹着盐水、两足直立、以骨骼支架撑起来的身体,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站立、行走,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奔跑。我们体液(占了身体80%的重量)里的许多化合物与分子跟远古海洋的组分大体一致。”
毋庸置疑,从演化意义上讲,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代表了自然选择所留下来的幸存者。它们均以某种方式揭示了演化史上的重大转变:从单细胞的细菌及其他生物个体,最终演化出人类高度的智力、语言、共情与合作能力。而且,一如达尔文所指出的:这种演化依然在进行之中。饶有趣味的是,跟人们脑子里固有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观念不同,威尔逊先生强调指出:在生物演化史上,每一次从较低的生物组织水平迈向更高的生物组织水平(比如,从细胞到生物体,从生物体到社会),都离不开利他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个悖论(即大转变的两难问题);但威尔逊先生坚信:这一悖论其实可以用自然选择驱动的演化来解释。这就是本书后半部分的内容。
本书余下的四章分别是:4.追踪漫长的社会演化过程,5.迈进真社会性的最后几步,6.群体选择,7.人类的故事。在这一部分,威尔逊先生指出,个体间简单的合作在生物界十分普遍,早在细菌中已见端倪;而众多较为进步的物种,均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与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物种(不到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的 “真社会性”,其中以蚁类、蜂类与人类最为著名。这些具有 “真社会性” 的类群,都占据了陆地生态系统中 “霸主” 地位。
“真社会性” 即一个生物群体组织内分化出可育(比如,蜂王、蚁后)与不可育(比如,工蜂、工蚁)的等级,并有了严格的内部劳动分工。野外观察和实验室研究显示,在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中,无疑 “自私者” 占上风;而在生物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中,由乐于合作者以及利他主义者占多数的群体,总是战胜由 “自私者” 占多数的群体。这也就是 “群体选择” 理论。威尔逊先生指出,当由同一个物种组成的不同群体竞争时,其成员的基因就会受到筛选,自然选择就驱动社会演化向着一定方向发展。
同样,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也表明,人类迈向 “真社会性” 的路径与其他 “真社会性” 动物如出一辙。社会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群体之间的竞争,其中不乏激烈的冲突(比如,部落、帮派、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常常十分血腥与残忍)。
总之,在本书中,谈及人类起源,对人类使用与制造工具以及脑容量增大等因素,威尔逊先生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强调了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人际间的合作。诚然,在当下民粹主义抬头、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下,威尔逊先生的这本新著,真可谓适逢其时,十分值得推荐给大家。达尔文主义的精髓,不只是狭隘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有广义上的 “群体选择”;而对具有了 “真社会性” 的人类来说,犹应牢记:恶斗必两败,合作即共赢。
本文摘自《苗德岁讲达尔文》,作者:苗德岁,译林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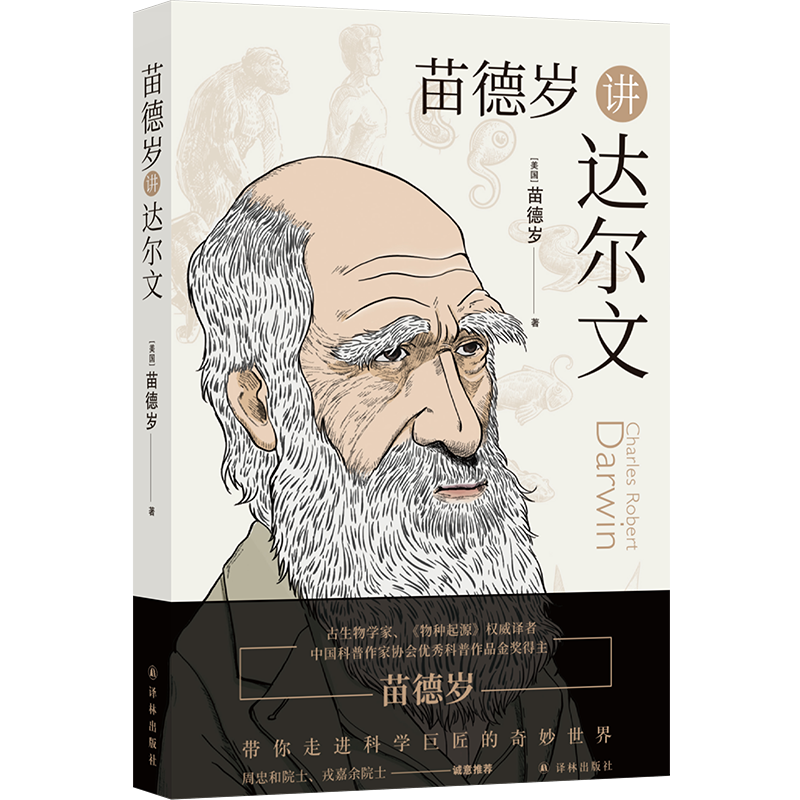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是亚洲首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古生物学家。”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