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 ● ●
问: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答:范岱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
引言
范岱年先生是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翻译家。1926年生于浙江上虞,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主编等职。他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虽长年身处逆境,他仍笔耕不辍,成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引入者、开创者和守门人,并对全国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岱年教授不仅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创立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还于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引入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成为了科学哲学在中国的老一辈领军人物。在本访谈中,他介绍了他和库恩、费耶阿本德、科恩等西方科学哲学家接触,引入科学哲学的过程。他还介绍了自己与洪谦、江天骥、邱仁宗、张华夏、龚育之、许良英、戈革、董光璧等中国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的交往,为中国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的学科史研究留下了重要资料。
西方科学哲学家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范先生,您不但见证了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还是科学哲学这个学科进入中国的主要引介人之一。请谈谈您跟西方主要的科学哲学家的接触。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我见到的第一个主要的西方科学哲学家是费耶阿本德。那是1979年的事,杜维明陪我去的,我们和费耶阿本德一起吃了顿饭。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对“四人帮”批相对论等很反感。我跟费耶阿本德讲了“四人帮”批相对论的事,结果他反问相对论为什么不可以批?
熊:呵呵,话不投机啊。他有没有在论著中引述过您跟他讲的事例?他觉得科学太强势了,应该被批判,包括被政治所批判、所干涉。他还曾为李森科辩护。
范: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当时还有一个左派杂志叫做《科学为人民》,很左的。那个杂志我还拿了几份。另外,我在哈佛听过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日本历史学家的一次讲演,他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应该完全重写。伯克利是很自由化的地方,有很多离经叛道的、颠覆性的观点,而哈佛很正统,所以像库恩这样的人,回不了哈佛哲学系。席文要回哈佛也回不去——他可能是人缘不好,得罪了一些人。
熊:听说席文的博士生很难毕业?
范:可能是,他这个人怪怪的。在美国很多人开车,他不开车,坐地铁上班,他可能眼睛有毛病。他很用功,有一次到中国来,到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资料。我觉得他资料掌握得很多,但他对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精神,比如中国的儒家传统,并没有掌握。
熊:文字资料跟实际情况通常有差距,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我们所看到的报告,跟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范:在美国时,我每天都翻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上面有时候没有中国的消息,有时候有一两条消息,都是关于中国的坏事,中国正面的事它们从来不报道。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来自报纸和电视,所以,那些没有来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了解是很片面的。
熊:报纸本来就是找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来报道,而有新闻价值的通常是坏事情。
范:我的那些外甥女一到中国来,就觉得与她们想象的不一样。她们以前把中国看得很落后,到北京后,一看大楼,比华盛顿的还高呢。
熊:在美国时,您有没有跟库恩接触呢?
范:有。1990年夏天,科恩在普罗维登斯租了一套房子避暑,让我也坐船过去,到那儿住一个礼拜。库恩的父亲很有钱,在那儿买了一所房子,库恩有三个兄弟姐妹,轮流去住。我们去的时候,库恩夫妇正好也在那儿,我们还一起吃过晚饭。我跟科恩接触比较多。纪树立、金吾伦跟库恩接触较多。
熊:金吾伦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译后记里讲到库恩去看他。
范:他跟库恩交往比较多,我跟科恩关系很密切。1990年库恩的那次生日会我也参加了,庆祝他生日。
熊:您对库恩的印象如何?
范:他这个人很腼腆。1990年,纪树立组织我们几个在波士顿的中国学者搞学术讨论,大家轮流讲,我讲梁启超,纪树立讲什么我记不得了。有一次请库恩讲,库恩很紧张,为了准备这个讲演,他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好。他不愿意一个人来讲,还让科恩陪他。讲完以后,他还要紧张一个礼拜。其实我们也就是随便讲讲,而他很当一回事。他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受到很多批评,大概因此变得很紧张。
熊:在西方,比如说在美国,他的学术地位到底究竟如何?
范: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么,后来想回母校,但哈佛没有要他——哈佛的哲学系没有让他回去,他也没有到哈佛科学史系去。他就改到MIT做教授。在哈佛的主要是那些搞分析哲学的人,譬如蒯因,他是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当然,库恩也有他的地位,他在美国科学哲学学会、科学史学会都当过主席。但是,也有一批人排斥他。我在波士顿大学听课,有一个叫希孟尼(Shimony)的教授,是学物理出身的,也搞科学哲学,他上课就批判库恩。好多人都批评库恩,但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因为他提出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很多物理学家觉得物理学发展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不厚,很多搞分析哲学的人就扣字眼跟他较真:你说不可通约,可科学还是有继承性什么的。
科恩对我影响很深。他在国际科学哲学界很有威望。《科学家传记》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条目是请他写的,他引了很多文献,写得很好,这表明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他希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间驾起桥梁,胸襟是很开阔的。1988年我去美国是他邀请的。波士顿大学有一个科学哲学论坛,每礼拜一次,请一个人讲,然后吃一顿饭。吃饭是自己掏钱。科恩对我们中国的访问学者很客气,不让我交钱,仍让我经常参加。回国之后,我一直和他交往,好几次我们中国的科学哲学会议我都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席,会议总结也请他来做。
进入21世纪后,我经常住美国——主要待在纽约,有时候到波士顿去看看科恩。有一次科恩送了我两本他们新出的关于尼采的文集,并说“你要看哦”。我就拿回来看。为了介绍这本书,2002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尼采的文章。[1]这篇书评出来后,许良英说:“尼采是个反动哲学家,你怎么搞他,没意思。”他后来也批评李慎之。李慎之听说BBC评选出的千年十大思想家里面有马克思和尼采,便也比较推崇尼采。许良英就写信给李慎之,说:“你怎么把尼采看那么高,罗素批评过他。”许良英还是老眼光,因为希特勒推崇尼采,就说尼采的哲学是法西斯哲学。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人也都很欣赏尼采,在俄国,列宁、托洛茨基也很看重尼采。
科恩晚年想把他所有的藏书(2万余册)全部捐给中国。他跟我们商量,我们说还是捐给清华吧。后来清华图书馆派了两个人到他那里,把书编了目再运回来。他也有个条件,他的书很系统,他不希望将其打散。他捐的书包括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维也纳科学哲学丛书等,还有很多期刊、好多画册。这些书要买的话,花几百万美元都买不下来。2007年,我发表了一篇专门文章介绍他[2]。

熊:尼采的作品不少,不同的人能读到不同的东西。一方面,他确实是很深刻的,另一方面,他的学说为法西斯所用也确有其事。
范:现在对尼采研究很多。我读了尼采的文集后,觉得他有一个思想还是很好的,就是不要迷信科学,虽然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要迷信它。科学经常运用还原论(简化论),而尼采说什么原子、电子,都是谎言,把自然数学化后,它跟真实有距离。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不要唯科学主义。他是批科学主义的。那个时候吴国盛等人批科学主义,龚育之、何祚庥捍卫科学主义。我后来就介绍了尼采的观点,说唯科学主义是应该批的。

在纽约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个叫巴比希(B.Babich)的女哲学家,她在纽约福德姆大学工作,学校离我们家很近。那本关于尼采的文集是她编的。她丈夫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的侄子。斯特朗到过延安,跟毛主席也有来往,她的墓在八宝山,我还拍了张照给她侄子。巴比希后来又编了一本关于诠释学科学哲学的文集。希伦是她的老师,在华盛顿大学当副校长,后来我与他联系,他把他的书都送给我。200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希伦的科学哲学。我先是研究库恩的历史学派,然后研究波普尔,然后又回来研究洪谦和逻辑经验论,再研究尼采,介绍希伦时我又搞了搞诠释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
熊:希伦在中国的影响小点。
范:大概是我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希伦的,也没有多大影响,现在有几个硕士生、博士生在研究他,但是他的书也没有翻译出来。
熊:重要的是得到教科书编撰者的注意,有教科书介绍其思想。我之所以知道库恩,是因为看了江天骥的《科学哲学导论》里的介绍,然后再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找库恩的原文来读。我对教科书介绍过的那几位科学哲学家,像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印象很深,别的人了解的就少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还要好的想法被编进教科书里。
范:你说的这几个人是科学哲学的标志性的人物。而希伦和罗伯特·科恩这些人没有进入教科书,因为他们的著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熊:您接触过波普尔、拉卡托斯没有呢?
范:我没有见过波普尔本人,查汝强有一次到伦敦去见过他。大概见过波普尔的中国同行就是查汝强了。哦,洪谦可能也见过他。但我在希腊开会的时候见过波普尔的学生沃特金斯和穆斯格雷夫。
熊:那您见过索罗斯本人没有?
范:见过,因为那次在武汉召开的波普尔会议。在北京饭店见的,因为股市突然出了问题,他后来没有去武汉。
熊:那您有没有机会见到拉卡托斯呢?
范:拉卡托斯死得早。那次我到希腊开会时,拉卡托斯已经死了。他很聪明。
熊:是啊,在那四个人里面,我觉得他的理论最精致。
范:他好像是从匈牙利去的,波普尔跟库恩争论时他很活跃,但是不久后他就去世了。
洪谦
熊: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家是不是洪谦?
范:王星拱比他还早[3]。但洪谦是最早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的。1991年回国后,我常去看洪谦,跟他交往比较多。科学哲学的发展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很大的影响。洪谦是维也纳学派领袖石里克的学生,石里克被刺杀后,他回到中国,宣传介绍维也纳哲学。那时候他很活跃,还跟冯友兰辩论。他写的文章后来变成一本小册子——《维也纳学派哲学》。
1949年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被说成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洪谦本来是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但不能再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也基本不能带学生了,所以他就编了几套哲学史的文献,古希腊、古罗马、法国、德国的哲学。对逻辑经验论他也有介绍,但那是作为批判材料介绍的。他一直很受压,许良英对他也不尊重,1956年搞自然辩证法十二年规划时,根本就没有提到维也纳学派,这是那个规划的一个大缺点。当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自然科学,还说要总结,其实并没有总结什么。
改革开放以后,洪谦是哲学所的学术委员,我也是学术委员。那时候我正好翻译了贝尔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这本书。这本书很有趣,把二十世纪前六十几年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成就列了一个表,总共六十二项。中国就一项,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府”。苏联有两项,列宁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还有苏联的计划经济。维也纳学派哲学是一项。有一次,我在哲学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这些情况,说维也纳学派哲学是二十世纪重大哲学社会科学成就之一。洪谦很高兴,过来和我握手。后来我们在《通讯》上介绍马赫等,洪谦也很高兴。我们对洪谦一直很尊重。
在美国时候我跟洪谦通信,洪谦在一封信中说,回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劝我不要回来。后来我还是回来了。回来了我经常到他家去,他就把他的全部稿件,发表和没有发表的英文、德文原稿都给我。

1992年洪谦去世。我跟梁存秀、胡文耕很快就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很长的一篇有关他的评传。这时他的学生高宣扬在香港编辑出版了洪谦的一个文集[4],不全,后来我跟梁存秀就把他的博士论文请人翻译了,编辑出版了一个更完整的文集[5]。我们编的这本文集,除了洪谦早年那本《维也纳学派哲学》[6],其余的都收集了。那本书商务印书馆已经出单印本了,所以我就把那本除外,其它的文章都有了。后来北大又要出一个《洪谦选集》[7],他的学生韩林合把我这本书拿去,再加上维也纳学派哲学,另外又加了一两篇文章,出了这本选集,其实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和梁存秀以前做的。
熊:洪谦是国内对哲学很有研究,研究非常深的人,一辈子的作品也就这么一点文章。
范:他到晚年还想再写几篇文章。1991年香港的周柏乔写了一篇文章[8],是对洪谦的评价。洪谦看了非常高兴,说:“我还有很多文章要写。”结果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
熊:德国海德格尔等人一辈子出了多少书啊?而洪谦……
范:洪谦1945年出了一本《维也纳学派哲学》,解放后他就基本不写文章了。在我们给他出的那本文集中,有一篇他解放后的文章没有收录——1955年他批判卡尔纳普的文章,迫于政治压力,违心地给卡尔纳普扣了一些政治帽子。后来他跟我讲,这篇文章不要收。所以我们就没有收。有一本西方哲学史,汪子嵩等在解放初编的,编者中本来是有洪潜(即洪谦)的名字的,1972年再版时[9],去掉了洪潜。
熊: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去掉?
范:可能也是后来洪谦不愿意加进去。这里对逻辑经验论是怎么讲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洪谦肯定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1957年鸣放的时候洪谦写了一篇文章“不要害怕唯心主义”,这篇文章我也没有收。本来是要收的,洪谦的夫人反对。当时洪谦已经去世了,洪师母说这篇文章不要收,她怕出事。后来韩林合编的时候,他就把这篇文章编了进去。1957年,哲学界有四个人受批判,金岳霖、洪谦、贺麟,还有一个人可能是郑昕。他们虽然没被划成右派,但也都挨了批,后来洪谦就吓得一个字都不敢写了。
熊:“批而不划”?是不是他夫人看了这篇文章心有余悸,过了几十年还害怕,所以就不主张收了?
范:洪谦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很活跃。他一到英国、奥地利就可以讲话了,心情非常舒畅,在国内他觉得很压抑。
熊:思想改造对冯友兰、金岳霖影响很大,使他们的思想有实质性的改变。洪谦有没有这种情况?
范:洪谦的思想变得少,不像冯友兰、金岳霖。最近我读了戴晴写的张东荪传,里面有一个场景:思想改造的时候,金岳霖去看望冯友兰,说冯的问题很严重。冯说我问题严重。然后二人抱头痛哭[10]。金岳霖他们对毛泽东很佩服,佩服他真是把天下打下来了。当时他们还觉得历史唯物论不错。
熊:他们觉得毛很伟大,毛让他们改造,他们觉得自己跟毛不一样,就真的改了?
范:张东荪好像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所以1949年政协开会,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另外是在政治上,他是希望跟美国建立关系,他反对“一面倒”。后来,他们全家因为那一张反对票而遭受沉重打击。1973年,张东荪去世。临死之前,他说,“我还是对的”。戴晴那本书没明说,他是讲自己哪里对了。是不要“一面倒”,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对了,还是没有投毛泽东的票对了?张是有点独立思想的。
洪谦是张东荪晚年在朗润园住时一直“敢”跟他来往的少数人之一,不时过来“一起谈谈哲学”。反右以后,他就是不吭声,文章也不写了,专门搞资料,编逻辑经验论文集,作为“批判材料”。他也不说话,只是翻译出来放在那里。改革开放以后他就开始写文章了。
熊:您觉得他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可以跟石里克等维也纳学派里面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
范:有些人还不承认他是维也纳学派正式成员呢。当时他还是个学生,跟那些著名哲学家当然没法比。他的博士论文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他说这篇文章还给海森伯看过。我读过这篇文章,没能看出作者有很高的水平。洪谦的作用在这里:他回国以后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接着他写文章,而且还跟冯友兰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回来就写了一本《维也纳学派哲学》,风头很盛的。当时国际上出了两本谈维也纳学派的书,一本是英国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长期被国际上作为逻辑经验论的基本教材;另一本就是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它于1945年出版,到解放以后就不让印了(直到1989年才重新出版),其影响有限。你想想,1945年到1949年,有几个人看哲学呢?
熊:您觉得他这个人看问题敏锐、深刻吗?
范:他本来是一个左派,他在抗战胜利后去英国访问,还跟共产党员王炳南等很熟,他在英国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知道了让他回来。那个时候他是亲共的,解放后王炳南还曾经想让他到外交部去呢。但是他不愿意当官。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确实觉得国民党腐败,同情共产党。解放后他想搞逻辑经验论,可逻辑经验论被称作是反动的,那个时候他心里是很压抑的。所以说思想改造时,在知识分子中他应该是偏左的。他以前可能比金岳霖,冯友兰更左一点。
熊:到七八十年代呢?
范:英国搞一个中英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院长。此学院每年在中国请几位英国有名的哲学家来上一个月课,用英文讲,用英文教材,讲完以后让同学用英文写心得,成绩最好的到英国去访问几个月。我当时很鼓励我的学生去,等于是留一次学,完全用英国的方式上课讨论,成绩好还可以出去一趟。后来澳大利亚也参加了,美国也参加,现在变成中英澳美暑期学院。
英国人搞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想用英国的分析哲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英国人的代表很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就是要用英国人的经验论的、分析的、理性的精神来影响中国人。
洪谦晚年重访欧洲,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对逻辑经验论作了反思。他觉得逻辑经验论哲学不具备完整的体系,它只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没有伦理学和美学。康德哲学包含三部分:纯粹理性批判是认识论,实践理性批判是讲伦理学,判断力批判是讲美学,一共三个方面。逻辑经验论只有认识论,所以这个哲学是不完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认识论,但是它有历史唯物论,有价值观——共产主义。所以,洪谦晚年有这个想法,他觉得分析哲学是不够的。
熊:我觉得分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消灭了传统的哲学。传统哲学关注的很多问题它都不关心了。它提出取消形而上学。
范:它强调认识的真假,不考虑实践、善恶这些问题。后来的逻辑经验论者也有搞伦理学的,不过这个学派的主要精力不放在伦理上面。洪谦还有一个体会,他说中国没有分析哲学的土壤。
熊:是啊。分析哲学是十分较真的。
范:而中国人会说,你何必那么较真呢?
熊:传统中国没有真理的观念,是非观也不十分强。
范:不像分析哲学,一个一个概念死抠。
熊:所以许良英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异类。他是非常较真的人,一真到底。
范:他喜欢跟人辩论。他跟王若水也要辩,跟李慎之也要辩,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人道主义,他就说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人道主义。谢韬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许良英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1991年回来,1992年碰到洪谦去世。1992年开了一次科学哲学的国际会议,主题是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科恩的“忆洪谦”,另一篇是我在那个会议上关于洪谦生平的发言。
熊:您觉得洪谦很值得纪念吗?
范:英国、奥地利对他都很重视,不管怎么样他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那时候英中暑期哲学学院请他当名誉校长。
熊:您说的国际会议是指中国召开的科学哲学会议?
范:是国际科学哲学大会资助的,在我们中国召开。邱仁宗早就在筹备,后来我们临时加了纪念洪谦的内容。
熊:正值洪谦学术盛年时,就不让做研究,所以他的哲学贡献也就很有限了。
范:后来1994年还专门开过一次纪念洪谦的会议,主题是“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这是奥地利资助的,同时也是纪念洪谦的会。这两个会都是国际性的会议,都用英文作为会议语言,都把科恩请来当学术委员会主任,最后会议总结什么的都是让科恩来做的。为什么请他当学术委员会主任?虽然邱仁宗英文也好,但毕竟不是母语。第一次会议出了论文集——《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第二次会议文集好像没有出来。我写了一篇洪谦与钮拉特的文章,后来在《学人》第七辑(1995)中发表了。
江天骥、邱仁宗和张华夏
熊:您跟江天骥教授熟悉吗?
范:很熟悉,科学哲学的元老是洪谦,而江天骥也是在美国拿了科学哲学的硕士学位回来的[11]。回来以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教科学哲学。
熊:难怪武大的哲学系强呢。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看到过江天骥的名字。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曾在抗战中从军。他是不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去留学美国的?
范:很可能是。他在解放前归国。1949年后,洪谦主要做翻译,基本上不教科学哲学了,而江天骥一直在教,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头一个科学哲学博士点就设在他那里。那时候国内做科学哲学的人不多,所以他的博士生答辩都让我去。他头一批博士生的答辩会就是我去主持的。另外,我们还在一起参加了好几个会。
熊:我读过他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范:那本书还是不错的,清晰、简洁,没有什么废话。1987年,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资助武汉大学召开一次纪念波普尔的会议,让牛顿·斯密斯(Newton Smith)和江天骥两个人来筹办,那次我去了,后来出了论文集Popper in China(《波普尔在中国》)。而且索罗斯有个长期计划,这类会议两年一次,第一次讨论波普尔,第二次讨论库恩,而且想把库恩本人也请来。结果1989年,要举行第二次会议前,国内出事了。
熊:索罗斯来参加第一次会议了吗?
范:索罗斯来了,都到北京了,结果收到一个电报,说股市出了问题,又临时走了,最后没能到武汉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序言是索罗斯写的,头一篇论文是我写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一位意大利资深记者到中国来访问,他向接待方人民日报社提出,想跟我聊聊。因为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建设开放社会,不再搞以前那种乌托邦工程,而是搞波普尔所说的渐进工程,摸着石头过河,进步蛮大。与此同时,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像中国这么大的、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开放、民主的现代社会,恐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现在看来,“封建”这个词用得不太对,应该改用“专制”。因为,中国自周朝结束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而是集权的郡县制了。
熊:汉朝、晋朝曾经分封过诸侯,有一些封建的味道,但那只是个临时的、短期的制度。
范: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专制传统。总的说来,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国的王朝很不一样。在欧洲,教会力量很大,贵族势力很强,均能制衡国王。而中国,帝王权力很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还能封神、封佛。回到江天骥来,他确实是个学者,好像还不是党员,而武大也一直很尊重他,所以,他在那里安安稳稳培养了不少科学哲学的学生。
熊:您跟他有私交吗?
范:没有多少私交,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邱仁宗经常参加他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我去得更多一点。而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组织的科学哲学会议。
熊:你们这几位是中国科学哲学的元老。江天骥年龄更大一点?
范:嗯。另外,江天骥是科班出身,在国外受过正规的科学哲学训练,而我和邱仁宗都是半途出家,我先学物理,邱先学外文,后来搞自然辩证法,再从自然辩证法改行搞科学哲学。还有个夏基松,搞科学哲学也比较早。他的硕士生兰征后来到武大跟江天骥念博士。夏基松先在南京大学,后来又到浙江大学,但不太活跃,作品不多,也很少参加我们的科学哲学会议。相比而言,张华夏就活跃多了。他是我们的积极分子,每会必到,而且每次都愿意跟人争论。他是我的好朋友。

熊:也是最早一批做科学哲学的?
范:张华夏是解放后毕业的。毕业后,他一直在高校从事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退休后的20年,他继续对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2015年,写出了《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这部高水平的科学哲学著作,很令我敬佩。邱仁宗可能是地下党员,后来在协和医科大学做马列教研室政治教员,他原来是外文系的,后来研究医学哲学。文革前为《研究通讯》写过好几篇关于医学哲学的文章。文革时,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文革结束后,我当自然辩证法室副主任时,就把他拉到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自然辩证法界,他是比较有成就的。他在协和,又和卫生部一些领导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对国内医学方面的伦理问题很熟悉。做研究,一要有理论上的创见,一要掌握材料。邱仁宗掌握了材料,思维能力也强,外文也不错,所以,他和国际上交流很多,他在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方面的成果,很得国际同行的认可。
熊:他掌握了一些独到的材料?
范:中国卫生界的事情他都知道。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国际交流部最早由查汝强负责,查汝强死后,改由邱仁宗负责。邱仁宗虽然年岁已高,现在仍很忙,每年都要出国多次。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
熊:老的自然辩证法界跟科学哲学科班出身的人关系如何?
范:科班出身科学哲学学者没有几个人,就是洪谦、江天骥。至于他们的学生,因为我也搞科学哲学,所以他们论文答辩我都去了。兰征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哲学博士,毕业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后被派到英国去做访问学者。接着,他通过我到波士顿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再后来,他就做生意去了。其实他要是回国,还是有学术前途的。卢风也是江天骥的博士生,大概是1991年毕业的,那时江先生在美国,他们就由张教授代带,他们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我主持的。
熊:黄顺基呢?
范:黄顺基是许良英的学生。抗战期间,许良英曾到桂林中学去教书,黄顺基是他那时的学生。他一直在搞自然辩证法,没有转。
熊:刘大椿呢?
范:刘大椿是黄顺基的学生。因为刘大椿是人大哲学系主任,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很多人都看重他。《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委会请他当副主任委员,《通讯》有好几位编辑是他的学生。山西大学成立科学技术哲学中心,也请他去兼职。
应当说,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原本是武大的科学哲学专业水平最高。江先生去世后,其地位有所下降,但还是相当强的。代表人物中,桂起权原来也是搞自然辨证法的,后来转到科学哲学。他很踏实,一直在那搞。现在当领导的是朱志方,他是江先生的博士生。武大的训练,分析哲学的基本功是比较扎实的,因为江先生是国外回来的,他很重视科学哲学新的文献。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是后来兴起的。
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的科学哲学界,除洪谦、江天骥等少数科班出身者外,其他都是从自然辩证法转过去的?
范:还有一些搞逻辑的,特别是搞数理逻辑的。中国有一些很不错的逻辑学家,譬如金岳霖、沈有鼎、王浩。周礼全也很聪明,但由于一直在国内,所以成就不够高。
熊:逻辑界也有转到科学哲学方向去的吗?
范:国际上有一个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会,然后它分成国际科学史学会,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中国逻辑学会和自然辩证法学会共同加入后者。所以上次意大利的会议,我是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特邀发言人,而周礼全的博士生王路则是中国逻辑学会的特邀发言人。逻辑学比较扎实、严谨,特别是数理逻辑。
龚育之
熊:自然辩证法本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文革过后,它扩展成一个“大口袋”或学科群。与此同时,你们还跟国际接轨,从国外引入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并因此而有不少相互交流。基本谈完科学哲学后,我想请您再谈谈整个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人和事。上次我们谈过于光远了[12]。今天谈谈龚育之吧。您和他的交往是不是也比较多?
范:在哲学所时,他是自然辩证法组的副组长,等于是我们的领导。我编《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时,每期的最后清样都要送他去看。他对刊物很关心,经常有具体的意见。
熊:您对他是什么印象?
范:他比较严谨,不苟言笑,不像于光远那样亲切、随便。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只是感觉他比较正统。后来,我右派改正了,当了通讯杂志社的副主编;他成了副部级干部,先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内先后任副理事长、理事长,而我是常委,有时在一起开会,吃饭时会一起聊聊天。从聊天可以看出,他读书很多,很博学,很关心思想界的动态。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肯定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他说:“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大陆在出版这本书时,把龚育之的评论放在推荐语的第一条。所以说,对于很多事情,龚育之都是知道的。

他有一次跟我说,1989年以后,他闲了一阵,他就研究邓小平的东西。后来邓小平南巡,他写了一本书,介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人民日报》社先把那本书作为学习文件发给大家,后来又把它收回了。大概官方对他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又不相信。我估计,他内心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在行政体系里面,他只是笔杆子,起草文件时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写。他写东西比较逻辑自洽一些,不像有的人,写的东西自相矛盾。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假如不受行政职务的牵累,专心致志做学问,肯定可以做出很多创造性的工作。
虽然龚育之和我交往并不深,但他对我的人生轨迹有重大影响。2007年他因病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有兴趣的可找来读读。

科学史
熊: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学科中,科学史的历史比较悠久。从民国时起,李俨、钱宝琮、张子高、刘仙洲、钱临照、竺可桢、陈桢等科学家都做过一些科学史方面的工作。
范:这些老科学家都有良好的古文素养,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顺便研究一下自己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这是很自然的事。譬如钱临照对《墨经》中的光学、力学很熟悉,竺可桢对中国的气候史比较了解。这类东西一搞出来就是国际水平,因为外国没有做相关工作的。抗战期间李约瑟到中国来,可能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国的这些老科学家,偏向于挖掘史料,没有搞史学理论的。
熊:您也做过不少科学史方面的工作,主持《通讯》以来,更和科学史界有深入接触。我也希望您谈谈科学史界的人和事。不求系统,但求亲历。您跟科学史所的人联系多吗?
范:科学史所开始刚成立的时候,仓孝和是所长,他让我当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当了一两届)。然后成立科学史学会,钱临照是会长,我是学会常务理事。科学史所的研究人员中,我认识杜石然,和许良英、席泽宗、李佩珊、董光璧比较熟,与戴念祖有一些合作关系。后来的刘钝所长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对我挺不错,我把文章送给他主编的《科学文化评论》,他都照登。董光璧是北大物理系的,后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干部,再后来到了你们科学史所。

熊: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跟科学史所的传统差别很大。
范:他胆子很大,人也很聪明。我约他在《通讯》写马赫。马赫这个人很了不起,既是力学家,又是哲学家,还实际是社会主义者。他崇尚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结果列宁写书骂他,将他打成敌人。我想让董光璧写马赫的人物评传,给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恢复名誉。起初董光璧还有点担心。我鼓励他写。与此同时,我还请胡作玄来写罗素的评传。
熊:后来他们写出来了吗?
范:写出来了,都登了。我想给这些人平反、翻案。我自己写了梁启超。蔡元培是很重要的人物,我让刁培德写。蔡元培原为国民党左派,跟陈独秀关系挺好,陈独秀死后,他还写了悼念文章,但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为什么如此我一直没搞清楚。
许良英和戈革
熊:科学史家里面,与您交往得最久、最深,对您影响最大的,肯定是许良英先生了。他的个性和您的差别很大。
范:我不如许先生那么自信。许先生很执着,他搞什么,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搞物理时,物理第一;搞自然辩证法时,他想让中国的自然辩证法超越苏联;后来他到科学史所工作,就是科学史家,不再搞哲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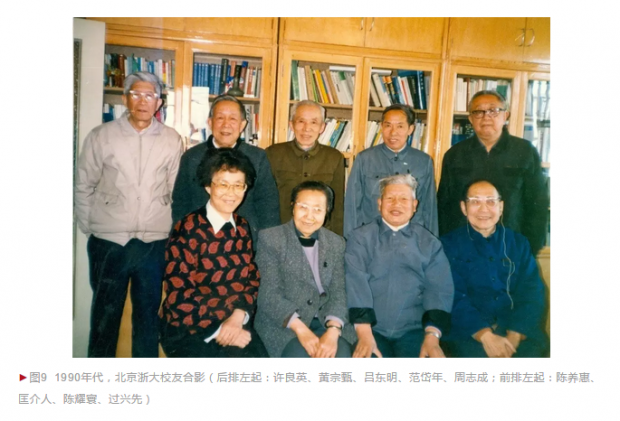
熊:戈革和许良英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戈革不时在报纸上刺一下许良英,这是为什么?
范:戈革只要有机会就点许良英,不但点许良英,还点许良英的学生。文革以前,他们两个人没有来往。文革以后,戈革去看许良英,还送许良英礼物。后来,在几件事情上许良英把他得罪了。一件事情发生在杭州开物理学史会议期间。当时我可能不在国内,戈革、许良英、陈恒六等一起去的。戈革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的文章。许良英说那篇文章不能发,不让他在会上讲,把他得罪了。争论的焦点是,许良英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戈革不同意,说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止一个,玻尔跟爱因斯坦相当,不能说爱因斯坦就比玻尔高。陈恒六评论说,好像是研究谁谁就最伟大。
熊:戈先生是怎么批评爱因斯坦的呢?
范:他主要讲了玻尔和爱因斯坦长达三十年的争论,现在看来玻尔更正确。
熊:这个观点是有依据的嘛。戈革资历和许先生差不多,许先生能够压制戈革,不让他发言吗?
范:戈革资历浅一些,他毕业比我还晚,解放时还在念研究生。还有一件事也让戈革对许良英不满。《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有一个物理学史部分,由钱临照任主编,许良英任副主编,我是编委,戈革也是编委。戈革分工写“海森伯”的条目,他把海森伯(W.Heisenberg)狠批了一下,说他和法西斯合作等。钱临照可能觉得没必要把科学家骂得那么凶,就另外请复旦大学的王福山教授(他是海森伯的学生,直接在海森伯下面做过研究,但他对物理学史恐怕是没有戈革研究得深)写那个条目,把戈革那个条目给否了。这是钱临照和许良英决定的。戈革因此很生许良英的气。戈革这个人很自负,他写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

熊:许先生也如此。他的文章也改不得。
范:我关于玻尔与中国的文章在《科学文化评论》发表了[13]。我认为玻尔和爱因斯坦各有长处,不能说谁更伟大。许良英看了这篇文章,没有对我这个观点提意见,大概是接受了这个观点。他提了另外一个意见。我在文章中说,吴有训讲不要批玻尔。许良英说,他亲耳听到的是,不要那么批海森伯。
熊:吴有训说的到底是哪句话呢?
范:不要那么厉害的批海森伯。这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当时许良英已经在科学史所了。吴有训在医院里,许良英去看他。吴有训说,对于海森伯这种影响很大的科学家,你们不要随便批。我原来以为吴有训讲的是玻尔。吴有训曾经说过,玻尔对中国非常友好,后来冼鼎昌到玻尔研究所,玻尔待他就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们翻译了一批科学家的著作,在序言、注释中对他们做了批评。
范:批海森伯比较厉害。我译的《物理学与哲学》的头一版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的序是许良英帮我写的,对海森伯批得很厉害,再版的时候就没有用那个序。许良英那个序写得很好,但批得也确实很厉害。
熊:戈先生和许先生当面冲突了没有?
范:好像没有当面吵过,只是后来就不来往了。而且,戈革一有机会就刺许良英一下,但许良英不理他。戈革总觉得许良英压了他,一个是在杭州没有让他讲,一个是这个关于海森伯的条目不用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戈革讲那个文章。我当时没在场,何成钧去了。许先生劝戈革时,所用的理由可能是那篇文章观点有问题,发表出来后会挨批。
熊:许先生批评人时不太注意场合,不给人留情面。
范: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戴念祖跟我很好,因我帮了他的大忙。他翻了两种《物理学史》,但他当时的译稿没有达到出版的水平。所以,M.V.劳厄的那本算是我们两个人合译的,弗·卡约里的那本算是他译我校。后面那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得了奖。因我帮了忙,戴念祖很感谢我。后来,许良英要来科学史所工作,他也积极帮忙促进。结果许良英一到科学史所就把他们这批搞古代科学史的给得罪了。一件事是,戴念祖写了一篇《爱因斯坦在中国》,开始许良英就不让他发,后来觉得有材料,还是将其收到了他和赵中立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好像一涉及到爱因斯坦,许良英就有点“你怎能没什么研究就写文章呢?”的味道。本来戴念祖对许良英去科学史所是很积极、很鼓吹的,后来他对许良英也很有意见。

许良英这个人啊,他搞什么,就觉得什么东西重要。在浙大物理系的时候,他就将“科学至上,物理第一”写在实验室门口。王淦昌还表示过欣赏。后来他搞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了,又把这看得最重要。到科学史所后,他又突出科学史,不谈自然辩证法了。他搞现代科学史,搞西方,认为自己所搞的东西很重要,看不起那些搞古代中国科技史的人。人家虽然主要是讲中国古代的成就,但搞了那么多年,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价值的。李佩珊是中宣部来的,到自然科学史所做副所长,后来以副研究员的身份退休,没有申请研究员职称。做古代史的那些人也太厉害了,不管怎么样,李佩珊编了《20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简史》,还写过一些论文,还是够格当研究员的,何况她还是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的理事。
熊:她不申请研究员职称,还是申请了没过?
范:她不申请。她怕在评审时这些人为难她,让她难堪,就没有申请。
熊:许先生与许多人的冲突都是源于个性。他不够随和,不太能求同存异,导致很多无谓的冲突。
范: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时,大家就都有点怕许良英,因为他不但是党员,还是党组很信任的人。他后来研究爱因斯坦,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熊:而且,似乎别的研究爱因斯坦的人,都没有他研究的好。至少得让他看过、认可了才能发表。是不是戈革也有类似的问题?他研究玻尔,似乎也认为别的对玻尔的研究都没有他的好。批评玻尔是不行的,说玻尔好也不一定行,因为没他说得好。
范:文人相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爱因斯坦和玻尔争得那么厉害,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彼此还是很尊重。爱因斯坦和玻恩交流时,有些话也说得很尖刻,像“我替你脸红”之类,但他们一直都有很深的友谊。
熊:我是这样想的: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爱因斯坦能解决一些难题,别人也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并不是能解决难题的人就能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譬如,我的相机出了故障,相机维修站没读过什么书的小青年能修好,可爱因斯坦未必能修好。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长处,虽然爱因斯坦很聪明,很伟大,但也不好说他就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因为别的一些杰出的人也有其聪明、伟大之处。
范:后来物理学的主流肯定是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很伟大,但他晚年搞统一场论就不成功,引力场和电场就是统一不起来,后来实际上是弱相互作用力和电磁力先统一,至于万有引力和强、弱相互作用力的统一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另外从培养人才来讲,玻尔的功劳确实要大些,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培养了多少人才!不过,玻尔的文章确实没有爱因斯坦的那么漂亮……
熊:那些人才是玻尔培养的吗?好多人都到玻尔那里去工作过,但他们未必是玻尔的研究生。量子理论起步于玻尔的原子模型,但后来的很多发展并不是玻尔做出来的。
范:所以关洪对玻尔评价很低,说玻尔的互补原理根本不是物理的东西。好像量子理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海森伯、狄拉克等人做出的。我的文章也提了此事。我批评了关洪。玻尔的原子结构是非常了不起的,用经典量子论解释了原子结构、量子态等,而且用光谱的观测资料证明原子结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爱因斯坦说这是一个神韵,以前光谱那么复杂,结果他用原子结构理论、电子态的能级把光谱全解释了……
熊:而且精确度极高。
范:要没有原子结构这个基础,量子力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后来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玻尔研究所有这个条件——谁量子力学做出成就了就请去。海森伯和泡利这两位大将开始都是玻恩的学生,后来讨论量子力学都是到玻尔那里去。海森伯关键的那一步,是他跟玻尔两个人讨论了好久以后才搞出来的。玻尔的贡献不是说我写文章,我署名,我领头,他就是和大家讨论。另外一点就是,哥本哈根学派是玻尔领导的。尽管泡利、海森伯这些人都参加了索尔未会议,但跟爱因斯坦争论都是由玻尔出面,他们这些小喽啰跟在后面,玻尔胜利时他们就高兴得很。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难题(光盒子的思想实验),玻尔当天解决不了,想了一晚上才用来解决,还用上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红移,证明测不准关系是正确的。
熊:玻尔确实是很有领袖才能是吗?
范:大家公认他是领袖,像海森伯、泡利都是承认的。玻恩有些郁闷,他很早就提出几率解释,而且海森伯提出量子力学时连矩阵都不知道,是玻恩告诉他这是矩阵,可玻恩得到诺贝尔奖很晚。可能当时物理学家们受决定论因果关观影响太深,对几率解释有保留。
玻尔提出原子结构理论,已经做出很大的成就,但原子中粒子的动力学(量子力学)还在摸索之中。他邀请一些青年才俊到自己的研究所访问,跟他们讨论问题。海森伯跟玻尔讨论,他们两个人在公园里谈,海森伯都头疼了,玻尔还一再向他提出问题,当时的思想是非常紧张的。后来薛定谔搞出波动力学以后,玻尔马上请他过去讨论,一直讨论得薛定谔也受不了了。
说起许良英,我想了五十年代初我们还在杭州时的一件事。有一天,许良英和我们聚会。他说:从事地下工作时,我们这些地下党员是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现在解放了,我们可以各奔东西,相忘于江湖,在不同地方、不同岗位各自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命运把我和他紧紧地绑在一起,终身都是相濡以沫。许良英还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all or none,非全则无。他确实是这种个性,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对理论如此,对人也是如此。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一生。
参考文献:
[1]范岱年.尼采和科学哲学.见:范岱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73-82页.
[2]范岱年.杰出的科学哲学家罗伯特·科恩与中国.见:江晓原,刘兵编.我们的科学文化——阳光下的民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9-17页.
[3]王星拱(1887-1949),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1910年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先入化学本科,后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18年归国,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总务长、安徽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著有《科学方法论》(1920年)、《科学概论》(1930年)等。
[4]洪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高宣扬编,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
[5]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范岱年、梁存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6]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7]洪谦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8]周柏乔.洪谦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学见地.哲学研究.1992(4):77-80.
[9]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内部交流版,2008年,396页.
[11]江天骥(1915-2006),哲学家、翻译家和哲学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后投身抗战。1945年赴美国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院。194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1948年至1952年受聘武汉大学副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工作,任副教授。1956年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后,他应聘回校任哲学系教授、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此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至1998年退休。
[12]详见:熊卫民.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2015(2):95-110.
[13]范岱年的《尼耳斯·玻尔与中国——有关历史资料汇编》分两期(2012年第2、3期)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