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前 言
2020年2月28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去世,享年96岁。这篇文章,初稿曾以 “弗里曼·戴森:科学家与作家的一生” 为题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 年第 3 期,也曾作为附录重印于戴森的中译本著作《一面多彩的镜子》,后又刊登于《数学文化》2015 年第 3 期和《数理人文》2016 年第 9 期,并在微信公众号数理人文与赛先生分期推送过。据一些热心读者和朋友(包括戴森本人根据英文版——感谢香港城市大学陈关荣教授斧正)的反馈,初稿中的某些错误现在得到了更正。《知识分子》获作者林开亮和“好玩的数学”授权,发布修订版,以纪念刚刚离开的戴森。
撰文 | 林开亮
In my lif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re family, friends and work, in that order. So my greatest contribution was to bring up six children who are all successful in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now raising families of their own. My work was not as important as that. Also, my work as a writer was probably more important than my work as a scientist.
[ 在我的生命中,三样头等重要的东西依次是:家庭,朋友和工作。因此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六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中都取得了成功并且拥有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工作并没有这等重要。而且,也许我作为作家的工作要比作为科学家的工作更为重要。]
——弗里曼·戴森,2012年11月21日给笔者的信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名字在中国也许已经不陌生。作为杰出的科普作家,他有广泛的读者。他有好几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处女作《宇宙波澜》[1] 甚至有三个译本,而邱显正的译本在2002年荣获了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发的首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全方位的无限》、《想象中的世界》、《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反叛的科学家》和《一面多彩的镜子》也先后出版了中译本。想必很多读者都为戴森的文笔所吸引,而对他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却未必很了解。本文将尝试解读这位集科学才能与人文修养于一身的大家。
现今的戴森即将九十二岁,仍在继续写文章、做研究,包括纯数学方面的一些有趣工作。十多年前,戴森接受南开大学数学所葛墨林教授的邀请访问中国,并游览了首都北京和古城西安。中国悠久的文化与飞速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扮演的角色寄予了厚望。这尤其反映在他于2013年7月26日回复给老朋友杨振宁的邮件中:
你写道,当我们年轻时,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现在我看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你可以因为能够有机会先后为这两大转变做出贡献而骄傲。留给我们儿孙辈的主要任务是,要见证这个转变和平地发生。
我常常想起你的美文《父亲和我》[2]。他 [3] 也必定会为之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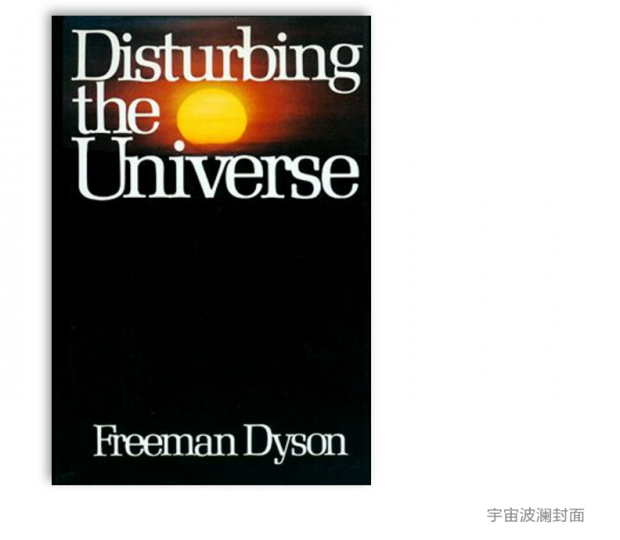
本节注释
[1] Dyson 1979.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New York: Harper & Row.
[2] 杨振宁 1991,“Father and I”,收入 C. N. Yang 2013. 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 World Scientific. 有中译文《父亲和我》,收入杨振宁《曙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即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杨武之,1896--1973,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28 年在芝加哥大学代数与数论专家迪克森(L. E. Dickson)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是在中国传播近代数学的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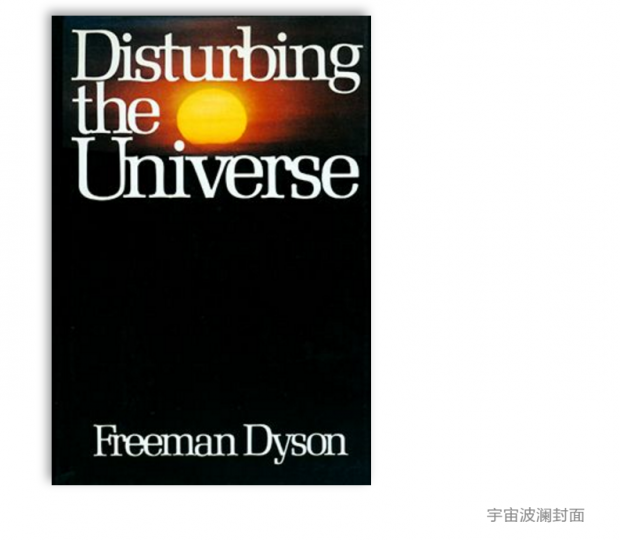
一、英才少年
弗里曼· 戴森1923年12月15日生于英国。母亲雅特琪(M. L. Atkey)是律师,在40岁生下爱丽丝·戴森(Alice Dyson),43岁生下弗里曼·戴森,之后一直以社会工作者为职。父亲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是音乐家,曾任教于英国历史悠久的温彻斯特学院,后来迁升为伦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乔治对科学很有兴趣,书架上有很多科学书籍,如怀特海(A. N. Whitehead)、爱丁顿(A. S. Eddington)、金斯(J. Jeans)、霍格本(L. Hogben)和霍尔丹(J. B. S. Haldane)的作品。这使得戴森从小就接触到科学。但戴森说,其实在成为科学家之前,他早就是作家了。因为他九岁时就写了一篇科幻小说。这篇未完成的处女作后来作为开篇收入到他的通俗文集《从爱神到盖娅》[1] 中。

戴森小时候非常迷恋凡尔纳(J. Verne)1877年的《太阳系历险记》(Hector Servadac)。他一直把它当作真的故事来读,到后来发现原来“一切都是编造的”时非常失望。不过,凡尔纳的风格激发了戴森本人童年时代的写作。这里展示了他小时候在笔记本里的一副创作。

戴森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非凡的数学才能。他在为《科学的面孔》[2] 所写的简短自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他还很小,还需要躺在婴儿床里睡午觉。但那一天他不想睡觉,于是用计算来打发时间。他计算 1+1/2+1/4+1/8+1/16+…,发现最终得数为2。然后,他又计算 1+1/3+1/9+1/27+…,发现最终得数为3/2。他再次计算了 1+1/4+1/16+1/64+…,发现最终得数为4/3。换句话说,他发现了无穷级数。当时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个奇妙的经历,他觉得这不过是他喜欢的一个游戏。
1936年,戴森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升入了父亲所执教的温彻斯特学院,直至1941年毕业。他与隆科-希金斯兄弟(H. Christopher Longuet-Higgins,Michael S. Longuet-Higgins)、赖特希尔(J. Lighthill)一起结成了 “四人帮”,他们后来都在各自的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都入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3]。克利斯朵夫·隆科-希金斯(1923-2004)是理论化学家,同时也是音乐认知学家。迈克尔·隆科-希金斯(1925-2016)是数学家和海洋学家,曾与几何学家考克斯特(H. S. M. Coxeter)合作过关于均匀多面体的著名论文 [4]。赖特希尔(1924-1998)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曾担任狄拉克(P. A. M. Dirac)与霍金(S. Hawking)之间的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 [5]。
温彻斯特学院不赞成逼迫有天赋的孩子提前学习高等数学与科学。教师认为学生自主地学习会更好,因而有意地放任学生,学生有许多时间可自由支配,戴森和其他男孩主要靠自学。戴森说,“四人帮” 之间相互学习的收获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
在戴森看来,学院设有极好的评奖机制。对每个年级,学院每年举行三次竞赛,优胜者将获得三十先令,但必须在学院的书店里花掉。戴森经常在竞赛中获奖,因而拥有了自己的藏书。从1937年至1940年,他一共赢得了19本书。这些书对他的兴趣发展及智力培养起到了决定作用,有些书甚至成为他一生的珍爱。其中最有影响的几本是:贝尔(E. T. Bell)的《数学精英》[6]、哈代(G. H. Hardy)与赖特(E. M. Wright)合著的《数论导引》[7]、朱斯(G. Joos)的《理论物理》和拉曼纽扬(S. Ramanujan)的《数学论文集》。

戴森为贝尔的数学科普书《数学精英》所深深吸引。他曾回忆道 [8]:
十四岁时我读了贝尔的《数学精英》。该书记载了许多伟大数学家的传奇故事。贝尔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同时也是很有天赋的作家。他令人信服地向读者介绍了数学界的精英。他懂得如何去打动情感敏锐的青少年的心弦。贝尔的书造就了整整一代的年轻数学家。尽管书中许多细节与事实不符,但主要情节是真实的。在贝尔的笔下,数学家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做错事,也有瑕疵。数学俨然成了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涉足的魔法王国。该书传递给年轻读者的信息是:“如果他们能做到,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贝尔的书激发了戴森成为数学家的抱负。他甚至有了这样的梦想,有一天要证明出著名的黎曼假设(Riemann Hypothesis)。
1939年9月3日,英国首相张伯伦被迫对希特勒宣战,英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圣诞假期里,为了弄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戴森开始自修一本比较高深的数学书,皮亚焦(H. T. H. Piaggio)的《微分方程》,是他同年在学校获得的奖品。戴森担心他可能会在战争中丧生,那样的话他甚至可能比贝尔书中最悲惨的数学天才伽罗瓦(É. Galois)还要悲惨,因为伽罗瓦毕竟在决斗之前就已经创造出不朽的数学成就。当时他满脑子里只有伽罗瓦决斗前的遗言“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 因此,戴森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数学中,每天从早上六点学到晚上十点,除了中午休息两个小时,每天平均学习长达十四个小时。虽然戴森自己乐此不疲,但却令他的父母很担忧。母亲引用了乔叟(G. Chaucer)笔下的牛津教士的话“一心专注求学问,无暇他顾出一声”,并警告他,长此以往将要生病甚至损坏大脑。而父亲则一再建议他放下书本,一起出去帮他干点农活以调剂放松一下。但戴森置若罔闻,继续沉迷于皮亚焦的《微分方程》中。圣诞假期快结束时,戴森已经完成了书上的近 700 道习题,差不多要大功告成了,因此他愿意抽空陪母亲一起散步。对此,母亲已祈盼多时了,而且早有准备。母亲当时说的话对戴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宇宙波澜》[9] 中引述如下:
我母亲是个律师,因而对人极感兴趣,她喜欢拉丁诗人和希腊诗人。同我讲话时,她先引用了一个原是非洲奴隶后来成为最伟大的拉丁剧作家埃福(T. Afer)的剧本《自虐者》(The Self-Tormentor)中的一句台词:“我是人,我绝不自异于人类。”这是她在漫长的一生中,直到九十四岁去世,一直奉为信条的箴言。当我们沿着泥沼和大海之间的堤坝漫步时,她对我说,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的信条。她了解我对皮亚焦的抽象美的渴望和热爱,但她要求我,在渴望成为一个数学家的过程中,不要丢失人的本性。她说:有朝一日你成了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却清醒地发现你从未有时间交过朋友时,你将追悔莫及。如果你没有妻子和儿女来分享成功的喜悦,那么纵使你证明出黎曼假设,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只对数学感兴趣,那么日后你将会感到,数学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有如苦酒。
如戴森在书中所说,“母亲的箴言已经逐渐深深地印入我的潜意识中,并且不时地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戴森还下功夫读了哈代和赖特的《数论导引》,并尝试证明书中的每一个定理。要知道全书共有400多条定理,而戴森当时还不满14岁!这本书培养起戴森对数论的浓厚兴趣,而哈代对戴森长达一生的影响也由此拉开序幕。
除了阅读自己的获奖藏书以外,戴森还与赖特希尔一起读了学院图书馆的另外两本书,怀特海和罗素(B. Russell)的《数学原理》与若尔当(C. Jordan)的《分析教程》。这两本书是赖特希尔的意外发现。他们很快判断出,《数学原理》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分析教程》则是打开现代数学殿堂之门的钥匙。他们一直很好奇,《分析教程》这本用法语写成的三卷本大部头高等数学教材怎么会放在学院的图书馆里。直到多年以后,戴森读到哈代的经典著作《一个数学家的辩白》时才找到合理的解释。哈代在该书中描述起《分析教程》一书对他的影响 [10]:
我永远也忘不了阅读这本伟大著作所带来的惊喜,对与我同一时代的许多数学家来说,这是第一个启迪。在阅读它的时候我第一次了解到数学的真正涵义。从那以后,我才走上了成为一位具有健康的数学志向、对数学具有真诚热情和抱负的真正数学家的道路。
哈代的感受必定引起了戴森的共鸣。后来戴森了解到,原来哈代在 40 年前也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哈代在这里过得不太愉快,因而他很少提及这个著名的母校 [11])。戴森一度猜测,也许正是哈代有意在学院图书馆留下了这本书,想 “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后来戴森升入剑桥大学,成了哈代的学生。但由于哈代高高在上难以接近,戴森没有勇气找哈代本人求证。1947 年哈代去世后,这也成了戴森的一大遗憾。
在学院的最后一个暑期,戴森的高中数学老师德雷尔(C.V. Durell)安排了几何学家裴多(D. Pedoe)来给戴森与赖特希尔做专门的辅导。裴多当时是十二英里之外的南安普敦大学的初级讲师,他是戴森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数学家。裴多后来曾追忆起17岁的戴森 [12]:
戴森问我还有没有比中学里的无穷级数问题更有趣的东西,因此我建议他研究将平面内由方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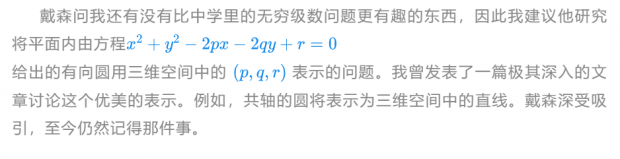
如戴森所说,虽然他没有成为几何学家,却从裴多身上学到了对几何风格的鉴赏力,从而把数学看作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科学。
戴森在学院还结交了比他大三岁的文艺青年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弗兰克对戴森的影响比学院其他任何人都要大。弗兰克在十五岁时就获得了学院诗人的称号。他对诗歌有很深厚的感情。对他来说,诗歌不仅是智力上的消遣,而且一直都是人们从无法言喻的灵魂深处淬炼出的智慧结晶。作为敏感的诗人,他更关心学院之外的大千世界,特别是当时正在进行着的西班牙内战与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戴森也因此从弗兰克那里第一次了解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道义问题。不过正如弗兰克离开诗歌就不能生活一样,戴森最钟爱的依然是数学。弗兰克不幸在二战中牺牲,其英雄事迹被戴森谱写进《宇宙波澜》“诗人之血” 一章。
本节注释
[1] F. Dyson 1992. From Eros to Gaia.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2] M. Cook 2005. Faces of Science. New York, London: Norton and Company.
[3] 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自然科学院的院士(人文科学的学者则可以当选为科学院的成员)。
[4] H. S. M. Coxeter, M. S. Longuet-Higgins and J. C. P. Miller, Uniform Polyhedra, Philos. Trans. R. Soc. Lond. A 246 (1954), 401--450.
[5] 杨振宁教授曾在给童元方教授的一封信里曾讲到赖特希尔的故事,见陈之藩《万古云霄》(北京:中华书局. 2014):他身体强健,而且喜欢做常人不能做的活动。曾经绕英伦海峡中一个小岛一气游泳一周,前后要十个小时。而且 1. 曾这样游过七次;2. 每次都独自游,不要有汽船跟随;3. 不穿橡皮衣;4. 第八次周游时去世!有人说他去世时自己知道已患癌症。……
[6] E.T. Bell 1937, Men of Mathematics.有两个中译本:《数学精英》(在 2004 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再版中更名为《数学大师》),徐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大数学家》. 井竹君等译. 台北: 九章出版社. 1998.
[7] 有中译本. 张明尧、张凡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8] M. Cook 2005.
[9] 戴森 1982.《宇宙波澜》. 陈式苏等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0] G. H. Hardy,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这本书有四个中译本:有两本译作《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分别是:王希勇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李文林、戴宗铎、高嵘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何生译(双语版),图灵公司出版,2020年;另一本译作《一个数学家的自白》,李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
[11] 关于哈代,可参考以下文献:斯诺(C. P. Snow)为《一个数学家的辩白》所写的序,中译文可见王希勇的译本;胡作玄,《哈代:不仅仅是数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 年第 4 期,62--72.
[12] D. Pedoe , “In Love with Geometry” ,College Mathematics Journal, Vol. 29, No. 3 (May, 1998), pp. 170--188.
二、剑桥大学
1941 年 9 月,戴森与赖特希尔双双进入了剑桥大学。由于当时英国处于非常时期,所有大学都安排尽可能短的课程以使学生尽快投入战争,很多学生只学习一年就离校从军了。戴森比较幸运,在剑桥听了两年课,到1943年才去服兵役。
剑桥大学只剩下年长的教授,数学系有哈代、李特尔伍德(J. E. Littlewood)、霍奇(W. V. D. Hodge)、莫德尔(L. J. Mordell)和伯西柯维奇(A. S. Besicovitch),物理系有狄拉克、爱丁顿、杰弗里斯(H. Jeffreys)和布拉格(W. L. Bragg)。学生也很少,在很多课程中,戴森与赖特希尔就占了听众中的一半,杰弗里斯的流体力学课甚至可怜到只有戴森一个学生。
这些教授中,以狄拉克最有名气。作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狄拉克在1931年出版了《量子力学原理》,这本书后来成为了物理学的圣经之一。狄拉克当时授课几乎就是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这让戴森很失望。因为这个课程完全缺乏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的意识,并且狄拉克也没有教学生如何做具体计算。戴森总是在课堂上提问,狄拉克往往需要停顿很久才能答复他,有一次狄拉克为了回答戴森的问题不得不提前下课。
戴森对哈代与李特尔伍德的课程非常满意。他注意到这两位著名的数学搭档风格迥异:哈代将数学作为成熟的优美艺术品展现给学生,而李特尔伍德则将数学作为智力拼搏的过程展示给学生。戴森更喜欢李特尔伍德的风格 [1]。不过,最能引起戴森共鸣的还是伯西柯维奇的风格。1993年,戴森为三联版的《宇宙波澜》中译本作了一篇序言,特别提到了伯西柯维奇对他的深远影响 [2]:
这篇中文版序让我有机会说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此书,我会添加哪些内容。首先我会添加一章内容探讨纯数学。纯数学是我们生活的宇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的科学生涯是以纯数学家开始的,对我思维方式影响最深的老师是俄国数学家伯西柯维奇。在我的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风格上,伯西柯维奇的痕迹清晰可见。…… 伯西柯维奇的风格是建筑式的。他依照层次分明的计划,从简单的数学元素中构造出一个微妙的建筑结构,而当他的建筑物完成时,整个结构通过简单的论证就引出意想不到的结论。…… 在四十年的物理研究之后,我最近又回到了纯数学。纯数学再度成为我科学活动的主要焦点。因此我更加了解了科学的艺术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科学家都是艺术家。作为艺术家,我以数学思想作为工具,奉伯西柯维奇为楷模。
1943年从剑桥完成学业以后,戴森服兵役投入到战争中,他为皇家空军做统计工作。直至1945年战争结束,他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但仍被要求继续服役一年,他被慨允在伦敦的皇家学院教学。战争吞噬了许多年轻的生命,学校很不景气,戴森几乎没有教学任务。他的上司查普曼(S. Chapman)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鼓励他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戴森于是成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数论专家达文波特(H. Davenport)讨论班上的常客。与剑桥的哈代、李特尔伍德、伯西柯维奇等形单影只的局面完全不同,达文波特的身边有一群年轻的研究生,研究氛围十分活跃。戴森跟达文波特提起他对西格尔猜想(Siegel’s Conjecture)的兴趣,得到了后者的极大鼓励。
其实当时戴森已经有了从数学转向物理的念头。之前他曾读到物理学家海特勒(W. Heitler)的专著《辐射的量子理论》,该书总结了 1930 年代末理论物理学的状况,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来解决基本问题,这深深吸引了戴森。但达文波特的友情和他在数学上给予的激励令戴森一时犹豫不决。于是戴森决定用西格尔猜想来决定他的方向:如果攻克了这一猜想,就继续做数学;如果失败了,就皈依物理。三个月的艰辛工作之后,戴森认输了。他虽然没有完全攻克西格尔猜想,但也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改进了西格尔早先的结果 [3]。
1945-1946年是戴森在数学上的黄金年代。除了在西格尔猜想方面取得部分进展以外,他还对另外两个问题——几何数论中的闵科夫斯基猜想(Minkowski’s Conjecture)与堆垒数论中的阿尔法-贝塔猜想( Conjecture)——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后两个问题都在主流之外,所以影响不大。(阿尔法-贝塔猜想在1942年为曼恩(H. Mann)证明,而闵科夫斯基猜想至今仍未解决,目前的研究进展可见 )
1946年服役结束以后,凭借出色的数学成就,戴森成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原打算重新学习现代物理,但慢慢意识到,他真正需要的是找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交谈,从那里获悉当前有哪些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样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数学功底探探深浅,看看自己是否适合搞物理。幸运的是,查普曼告诉他,在剑桥恰好有他要找的人:克默尔(N. Kemmer)。
克默尔曾受教于苏黎世大学的泡利(W. Pauli)和温策尔(G. Wentzel),他将从恩师那里学到的量子场论悉心传授给了戴森。量子场论主要是狄拉克、海森堡(W. Heisenberg)、泡利、费米(E. Fermi)的创造,其行家大多是欧洲人。在当时,懂得量子场论的人寥寥无几,而量子场论的书只有一本问世,作者就是温策尔。戴森从克默尔那里了解到其重要性,掌握了一手绝技,这对他以后从事物理研究有莫大的好处。克默尔极为耐心地指导戴森,给他详细解释了温策尔书中的难点,并让戴森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量子场论提供了以一种自洽的数学方式来描述大自然的关键。戴森一生阅人无数,他说克默尔是他见过的最无私的科学家。
虽然有克默尔的指点,但有更多的因素促使戴森想离开剑桥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戴森在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邂逅了流体力学专家泰勒(G. I. Taylor),二战期间他曾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于是戴森打听起美国哪个地方适合做物理。泰勒立即回答说:“噢,那你应该投奔到康奈尔大学汉斯·贝特(Hans Bethe)的门下,那是战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所有聪明人向往的地方。” 在泰勒的热心推荐下,1947年戴森只身前往美国。
有趣的是,就在戴森决定从数学转向物理的同时,剑桥的另一个人却决定从物理转向数学,就是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哈里什-钱德拉(Harish-Chandra)。哈里什-钱德拉是印度人,来剑桥追随狄拉克做博士,因为缺乏狄拉克对物理那种神秘的 “第六感”,而最终离开了物理。哈里什-钱德拉后来随导师狄拉克一起访问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戴森,他跟戴森曾说道:“我为数学而离开了物理学。我发现物理学乱七八糟、不严格、难以捉摸。” 戴森回答说:“恰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离开了数学而投入物理学的怀抱。”
本节注释
[1] 李特尔伍德也有一本著名的通俗数学书 A Mathematician's Miscellany. 新版本 Littlewood's Miscellany 有中译本《Littlewood 数学随笔集》. 李培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 戴森 1998.《宇宙波澜》. 邱显正译. 北京: 三联书店.
[3] 最终的荣耀归于戴森的同胞罗斯(K. Roth)。见维基百科(Wikipedia)中的条目:Thue–Siegel-Dyson-Roth 定理。
三、成功转行
1947年9月,戴森入学康奈尔师从贝特。他立即发现,自己来对地方了:在整个康奈尔大学,居然只有他一个人懂量子场论。量子场论是一个成熟的数学构造,当初欧洲人创造这个理论时,更多的是基于对数学美的考虑而不是解释实验方面的成功,因此大多数持实用主义的美国物理学家不愿费力去学它。但后来发现,有很多实验需要用量子场论才能解释,这使得学习量子场论成为必要。戴森的到来恰逢其时。因此,戴森一边跟指导老师贝特与聪明的年轻教员费恩曼(R. P. Feynman)学习物理,一边又教他们如何处理量子场论的问题。戴森带去的技巧可以计算一些原子碰撞过程,而得到的数据又能够为实验证实,因此他立即得到了师友的青睐。
贝特当时关心的是量子电动力学 [1]中的问题,该理论致力于精确描述原子和电子如何发射和吸收光子。现在回顾起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在量子力学诞生20多年之后的1947年,人们对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粒子,氢原子和光量子,都没有一个精确的理论!不过已有突破性进展,物理学家兰姆(W. Lamb)同年测出了所谓的 “兰姆移位”,引起同行们的高度关注。同年 6 月,美国科学院在纽约谢尔特岛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兰姆移位及相关问题,这是历史上的盛事,虽然与会者只有 24 位,但都是一流人物。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重正化的想法。贝特就是利用这一想法,在会后返回康奈尔的火车上粗略计算出兰姆移位。他给戴森的主题,就是深入探究重正化,给出严格的处理。这在当时是最热门最前沿的理论问题。
1948-1949年,戴森遵循贝特的建议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一年。这是戴森科学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那一年,年仅25岁的戴森做出了他在物理学上的最重要的贡献——量子电动力学的重正化,一年之间,他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物理学界一颗闪亮的新星。他成功转行了!
在当时的美国物理学界,研究重正化的活跃分子有两个:哈佛的施温格(J. Schwinger)与康奈尔的费恩曼。他们都是物理奇才,但品味与风格很不一样。[2] 1948年,凭借出色的数学天分与人际交往能力,戴森直接从费恩曼与施温格那里学到了他们各自对量子电动力学的处理方法,并完美地吸取了两个方法的优点,从数学上给出了量子电动力学重正化的一个自洽表述。在《宇宙波澜》第六章中,他曾回忆起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美妙瞬间:
第三天,当巴士徐徐驶过内布拉斯加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我已经两周没有思考了的物理,此刻却排山倒海一股脑儿地涌进我的脑海里。费恩曼的图像和施温格的方程式,在我脑海里开始自动地一一对应,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我生平第一次,可以将这两个观点连接在一起。有一两个小时,我把那些片段不停地重组再重组,忽然我领悟到,他们其实可以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我手头没有笔和纸,但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根本不需要写下来。费恩曼和施温格其实只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看待同一个思想;如果将他们两人的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兼顾施温格的数学上严谨与费恩曼的应用上灵活的理想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
在了解到日本物理学家朝永(S. Tomonaga)的早期贡献后,戴森精心创作了论文《朝永、施温格和费恩曼的辐射理论》,这成为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或多或少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理论是属于朝永、施温格和费恩曼这三个人的,戴森只是做了简单的整合。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对戴森的工作有高度评价[3]:
重正化纲领是物理学的伟大发展。这个理论的主要缔造者是朝永、施温格、费恩曼和戴森。1965 年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朝永、施温格和费恩曼时,我就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因为没有同时承认戴森的贡献而铸成了大错。直到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朝永、施温格、费恩曼并没有完成重正化纲领,因为他们只做了低阶的计算。只有戴森敢于面对高阶计算,并使这一纲领得以完成。在他那两篇极富洞察的高水平论文里,戴森指出了这种非常困难的分析的主要症结所在,并且解决了问题。重正化是这样一种纲领,它把可加的减法转化成可乘的重正化。其有效性还需要一个绝非平凡的证明。这个证明是戴森给出的。他定义了本原发散性、骨架图以及重叠发散等概念。利用这些概念,他对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完成了量子电动力学可以重正化的证明。他的洞察力和毅力是惊人的。
这里杨振宁提到的两篇论文就是《朝永、施温格和费恩曼的辐射理论》及其续篇《量子电动力学的矩阵》[4]。杨振宁先生曾在给笔者的邮件中特别指出,这两篇论文各有其重要性:第一篇论文证明了费恩曼图的正确性,而在此之前费恩曼仅仅提出了构想;第二篇论文则攻克了高阶计算的难题,登上了朝永、施温格和费恩曼此前从未达到的高度。后来大家差不多都认同了这样的观点:与朝永、施温格和费恩曼一样,戴森也是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这尤其体现在施韦伯(S. S. Schweber)1994年出版的《QED及其缔造者:戴森、费恩曼、施温格和朝永》[5]一书中,该书第九章专门介绍了戴森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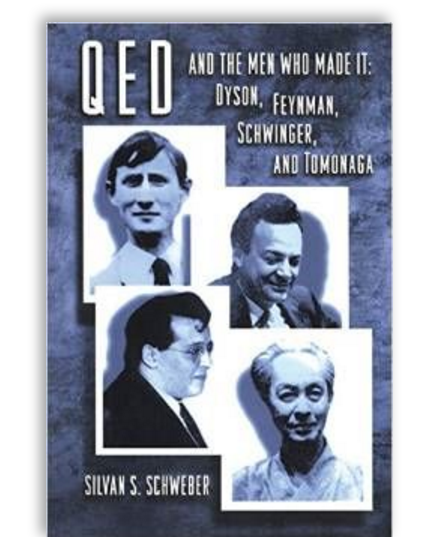
对戴森未能评上诺贝尔奖深表惋惜的,还有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温伯格认为,“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 ‘耍了(fleeced)’ 他”。但戴森对无缘诺贝尔奖并不遗憾。他说:“有一点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正确 [6]:为了获得诺贝尔奖,你必须有持久的注意力,要抓住一些深刻而重要的问题,至少坚持十年。但这不是我的风格。” [7] 这句大实话切中肯綮,不由让人联想起杨振宁先生论述科学家的风格与贡献之关系的一段著名论断 [8]:
在创造性活动的每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品味,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品味和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品味和风格竟然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如此关系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物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有它的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恶,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品味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绘画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以上这段话也是戴森深为欣赏的,因为他在纽约石溪为杨振宁荣誉退休举办的晚宴讲演《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9] 中也引用了这段话。戴森很清楚,他本人就是对 “品味和风格决定贡献” 的一个明证。
再度借用杨振宁先生常说的一个词,我们可以说,戴森在这一年完成了他作为年轻人的 “猛冲(push)”。一个重要的结果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J. R. Oppenheimer)给了他长期研究职位,这对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难得的。此后,奥本海默一直都很器重戴森,甚至期望他成为新的玻尔(N. Bohr)或爱因斯坦。然而,这不是戴森的风格。戴森曾经这样评价这位待他如父亲一般的长者 [10]:
奥本海默对物理学有着真正的终生不倦的热情。他总想持续不断地努力去认识自然界的基本秘密。我因为没有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令他失望。当他一时冲动地指定我担任研究院的长期职位时,他希望自己得到的是一个年轻的玻尔或爱因斯坦。如果那时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告诉他,迪克[Dick, 费恩曼的名字Richard的昵称]才是你要的人,我不是[11]。我曾经是并且一直是一个问题解决者而不是思想创造者。我不能像玻尔和费恩曼所做的那样,一坐好几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一个深奥的问题上。我感兴趣的不同事情太多了。
本节注释
[1] quantum electrodynamics,常缩写为 QED;而在数学中,Q.E.D.则常用来表示证明结束,它是拉丁文 quod erat demonstrandum(此即所欲证)的缩写。
[2] 杨振宁先生在 Julian Schwinger 一文(收入 C. N. Yang, 2013. 中译文《施温格》收入《曙光集》)中对费恩曼与施温格做了以下有趣的评论:费恩曼和施温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各自都作出了许多深刻的贡献。他们都出生于 1918 年。但就个性而言,他们几乎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我常常想,人们也许可以写一本书,标题为《施温格与费恩曼:一项比较研究》:百分之二十的情感外露的搞笑能手(impulsive clown),百分之二十的不守成规的行家(professional nonconformist),百分之六十的聪明物理学家(brilliant physicist),为了成为伟大的表演家,费恩曼(Feynman)所付出的努力,与他为了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付出的努力几乎一样多。腼腆,博学,用精雕细琢的优美语句演讲和写作,施温格(Schwinger)是有修养的完美主义者(cultured perfectionist)和极内向的绅士(quite inward-looking gentleman)的典范。
[3] C.N. Yang 1983,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W.H. Freeman & Company.
[4] F. J. Dyson (1949). "The radiation theories of Tomonaga, Schwinger, and Feynman". Phys. Rev. 75 (3): 486–502; "The S matrix in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Phys. Rev. 75 (11): 1736--1755.
[5] S. S. Schweber 1994. QED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Dyson, Feynman, Schwinger, and Tomonag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得奖(工作发表一年之后立即得奖)也许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杨振宁先生对此曾做过分析,可见刘钝、王浩强,爱因斯坦、物理学和人生——杨振宁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2005 年(第 2 卷)第 3 期,72--89。
[7] 见维基百科中的戴森条目:
[8] C. N. Yang 1983.
[9] 戴森 1999.“Chen Ning Yang,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有中译文,《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收入杨振宁 2008. 重刊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中华读书报》。
[10] 戴森 1982.
[11] 可以补充的是,根据费恩曼在《你真逗,费恩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中的自述,高等研究院的元老确实对费恩曼有如此期许,并且给费恩曼发过聘函,但被费恩曼拒绝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费恩曼不单单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个演员,讲台是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舞台。更重要的一点是,费恩曼曾明确表示:“I have no responsibility to be like they expect me to be. It’s their mistake, not my failing.”
四、康奈尔的教训与普林斯顿的救赎
1949-1951年,戴森回到英国,在伯明翰大学担任研究员。物理系主任派尔斯(R. Peierls)接待了他。在伯明翰,刚刚完成博士学位的萨拉姆(A. Salam)打电话给他的 “英雄” 戴森,请求拜访。这次会面激发萨拉姆推进了戴森关于重正化的工作,开启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
1950年,戴森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的数学家胡贝尔(V. Huber)结婚。
1951年,戴森返回美国。为了吸引戴森,康奈尔大学在戴森没有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破格聘他为物理教授。1951-1953年,戴森在康奈尔一边讲课,一边指导麾下的博士后和研究生做理论计算。他的讲义《高等量子力学》帮助了许多人进入这个领域,六十多年以后作为书籍正式出版了[1]。而在指导学生方面,他认为是极其失败的,以至于决定从此以后不带研究生。[2]
故事是这样的。当戴森与其学生取得了一些进展以后,他去芝加哥大学拜访这方面的专家费米。戴森很自豪地将他们的计算结果呈给费米看,期待费米的认可与激动反应。令他意外的是,费米竟然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平静地点评到,“计算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我所乐意的,是基于清晰的物理图像;第二种是基于严格的数学构架。而你的计算,都不是。”对于费米的批评,戴森心悦诚服。事实上他们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也不是特别吻合。1999年,在费米的学生、同时也是戴森的老同事杨振宁的荣休晚宴上,戴森心存感激地回忆起费米曾给他上的这关键的一课 [3]:
……虽然我不是费米的学生,但我有幸在学术生涯的关键时刻跟费米谈了二十分钟。我从这二十分钟里所学到的,比我从奥本海默二十年里所学到的还要多。…… 在这二十分钟里,他脚踏实地的见识省掉了我们好几年的无谓计算。
回到康奈尔,戴森意识到,学生这两年的功夫白费了,对此他非常愧疚。这给他投下了极大的阴影。为避免再度误人子弟,他决定不再带研究生。在康奈尔,戴森还与年轻的华裔数学家钟开莱有过学术交往,他解决了钟开莱向他提出的一个数学问题。
将戴森从沮丧与内疚中拯救出来的是奥本海默的聘约。1953年,戴森告别康奈尔来到普林斯顿,而立之年的戴森被聘为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应该说,戴森在这里如鱼得水,找到了家。《规范理论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的作者、台湾《中国时报》的前主笔江才健先生曾经在一篇对戴森的访谈 [4] 中问起他对高等研究院的看法:
江才健问:我记得杨振宁由芝加哥大学来这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以前,他的老师费米告诉他,说这里像一个修道院,可以待一阵但不能久留。杨振宁在此待了十七年而您却待了四十年,对于费米的话,您有什么看法?
戴森答:这因人而异。我想杨振宁离去是对的,因为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天地,成就更大的事业。对我来说,留在这里很好,因为我不是一个帝国建造者,我在此很开心,花时间于做研究与写书,我很满意。虽然年岁日老,但可以一直维持我的活力。
能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修道院里工作,当属戴森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戴森在高等研究院结交了许多科学同仁。例如,在研究院的同事与访问学者中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梅塔(M. L. Mehta)、约斯特(R. Jost)、勒纳(A. Lenard)。与戴森交流频繁的还有附近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维格纳(E. P. Wigner)、伯格曼(V. Bargmann)、李布(E. H. Lieb)等。戴森的许多工作就是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讨论而成型的。
1957年,一个偶然的原因——英国政府不承认戴森在瑞士和美国生的孩子,因而不给他们发护照——导致戴森最终加入了美国籍。戴森在《引路人》[5] 一文中写道:“我原本是英国人,只是阴差阳错才加入了美国籍。我同时为这两个国家而骄傲。” 笔者曾向戴森请教了英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他答复说:
英、美两国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英国历史更悠久、文化更灿烂,但对生活持悲观态度。而美国有更多样化的公民,科技强盛,而且为年轻人提供了许多机会。最明显的一个差别体现在对待游戏和竞技体育的态度上。英国的小孩受到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成为一个大度的失败者,竞争时必须确保公平,失败时必须不失风度。而美国的小孩受到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成为胜利者,要想方设法地赢得胜利。这两种文化都很珍贵。我很高兴这个世界同时保留了它们的存在空间。
本节注释
[1] Advanced Quantum Mechanics, World Scientific, 2007.网上有电子版
[2] 戴森本人并没有博士学位,因此在数学家系谱(M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里没有戴森的信息。贝特可以算作戴森的指导者(mentor),但他们不是正式的导师-研究生关系。戴森之成才,主要是靠自学。
[3] 戴森 1999.
[4] 江才健 1998. 《戴森:科学是更接近艺术而非哲学》. 台湾《中国时报》1998 年 1 月 30 日(社会综合版).
[5] Dyson 1992.
五、后续的物理与数学工作
美国数学会 1996 年出版的《戴森论文选集及评注》收录了他直到 1990 年为止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该书模仿了杨振宁 1983 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的格式,将 49 页的评注集结在一起作为开篇。正如杨振宁的评注描述了杨振宁之所以成为杨振宁,戴森的评注也描述了戴森之所以成为戴森。
《戴森论文选集及评注》中收入的工作分为三个领域:数学、物理、工程学与生物学。我们这里只介绍他的物理与数学工作。
在戴森 1948 年之后的所有物理工作中,值得特别书写的有两笔。第一是 1961 年关于随机矩阵的工作,是戴森与其创立者维格纳交谈的结果。对戴森而言,这个工作令他极为兴奋,他在《戴森论文选集附评注》[1] 中写道:
1961 年我在布鲁克海文度学术假,以极快的速度写完了三篇系列论文。好像我每天都在发现新的要解答的问题。每一个优美的等式在第二天又引出另一个更加优美的等式。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戴森仍然不时地回到这一主题。由于维格纳、梅塔、高登(M. Gaudin)、戴森等人的努力,随机矩阵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而且直到现在都很热门。常常被传为美谈的是,戴森与造访高等研究院的数论专家蒙哥马利(Hugh Montgomery)的一次偶然交谈,促成他们发现了随机矩阵与数论中的黎曼假设之间的微妙关联。
戴森的第二个重要工作属于统计物理。1965-1966 年他与勒纳合作,首次从数学上严格证明了物质的稳定性。这个问题在一年前由费希尔(M. Fisher)和吕埃勒(D. Ruelle)作为悬赏(香槟一瓶)问题提出。戴森与勒纳用到的数学技巧源于他 1957 年对李政道、杨振宁的一项工作之改进。戴森与勒纳将近 40 页的复杂证明,在 10 年后被李布和瑟林(W. Thirring)简化到不足 3 页。对此,戴森在《戴森论文选集附评注》中反省到:
为什么我们的证明如此糟糕而他们[李布和瑟林]的证明如此优美?原因很简单。我和勒纳的证明是从一些数学技巧出发,在不等式的丛林中披荆斩棘,没有任何来自物理方面的想法作指引。而李布和瑟林是从一个物理思想——物质之所以稳定,是因为经典的托马斯-费米原子模型(Thomas-Fermi model)是稳定的——出发,寻求合适的数学语言将这一思想转化为严格的证明。当我在剑桥做学生时,数学家李特尔伍德一次曾在课堂上讲,第一流的数学家是那些发表糟糕证明的数学家。第一流的数学家发表糟糕的证明之后,第二流的数学家研究细节并给出更好的证明。物质的稳定性的两个证明为李特尔伍德的格言提供了一个反例。李布和瑟林找到了好的证明,他们既是第一流的数学家,也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我们的糟糕证明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激励了李布和瑟林去寻求更优美的证明。
虽然身在主流数学之外,戴森在数学界也颇有影响。总的说来,数学家更欣赏他的数学观,因此戴森常常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做演讲。例如,1965 年,他受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协会邀请,做了题为 “群论在粒子物理中的应用”的冯·诺依曼讲座(John von Neumann Lecture)。1972 年,他受美国数学会邀请,作了题为 “错失的机会” [2] 的吉布斯讲座(Josiah Willard Gibbs Lecture)。在吉布斯演讲中,戴森举了很多例子有力地表明,数学家由于与物理学家的疏远而错失了许多重要发现(例如麦克斯韦(Maxwell)方程中所隐含的狭义相对论原理)的机会。戴森以他本人的教训——错失了独立于数学家麦克唐纳(I. G. Macdonald)发现模形式与仿射李代数之间的奇妙联系的机会,“而这仅仅是因为数论学家戴森和物理学家戴森没有彼此沟通” ——现身说法,呼吁数学家多与物理学家对话,一起推动科学研究。
戴森的演讲才能也许受到了马丁·路德·金(M. L. King)的激发。他在《宇宙波澜》一书中曾提起马丁·路德·金在 1963 年 8 月 28 日所做的 “I have a dream” 的著名演讲 [3]:
马丁·路德·金讲得像《旧约全书》里的预言家。我离他极近,听他演讲时我哭了,哭的也不止我一个。“I have a dream.”他在向我们描述他关于和平与正义的展望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我在那天夜里写的家信中写道,“我随时准备为他蹲监狱。”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听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演讲,只知道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一次演讲。我更没有想到马丁·路德·金会在五年之后遇刺身亡。
1987 年,伟大的印度传奇数学家拉曼纽扬百年诞辰,戴森因为早年对拉曼纽扬的工作有过研究而受邀参加学术纪念活动。他所做的演讲是“漫步在拉曼纽扬的花园”。在演讲中,他希望数学家与物理学家关注拉曼纽扬生前的最后一项卓越发现——仿西塔函数(mock functions)。他充满寄托地说道(令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
我的梦想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年轻的物理学家实现超弦理论所预言的内容与大自然的事实之间的对应,从西塔函数(functions)扩展到仿西塔函数。
十五年之后的 2002 年,荷兰青年数学家兹威格斯(S. Zwegers)在德国波恩马普数学所数学家察吉尔(D. Zagier)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仿西塔函数”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2008 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数学家布瑞曼(K. Bringmann)与小野(K. Ono)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回应了戴森的呼吁,部分实现了戴森的梦想。与戴森的预言更契合的,是华裔女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程之宁(Miranda Chih-Ning Cheng)及其合作者在 2012 年提出、并由小野等人在 2015 年证明的 “伴影月光猜想(Umbral Moonshine Conjecture)”。这一点连程之宁教授本人也是同意的,她告诉我她当初提出这个猜想时并没有想到戴森的话。戴森的数学远见由此可见一斑。
2008 年,戴森为美国数学会的爱因斯坦讲座准备了以 “飞鸟与青蛙(Birds and Frogs)” 为题的演讲。讲座因为戴森生病而临时取消了,但讲稿 [4] 发表了。该演讲的基本观点取自《全方位的无限》[5],但立意更高,戴森提到了许多有趣味有哲理的话题。戴森在开篇写道:
有些数学家是飞鸟,有些是青蛙。飞鸟在高空翱翔,俯瞰数学的广大领域,直至遥远的地平线。他们乐于统一我们的思想,并且融合来自数学大地上不同部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青蛙生活在泥沼中,只能看到生长在附近的花朵。他们以特殊对象的细节为乐,在一段时间只解决一个问题。我碰巧是只青蛙,但我的许多最好的朋友都是飞鸟。我今晚演讲的主题就是“飞鸟与青蛙”。数学既需要飞鸟也需要青蛙。数学是丰富的和美丽的,因为飞鸟赋予它开阔的视野,青蛙赋予它错综复杂的细节。数学既是伟大的艺术,又是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把概念的普遍性和结构的深刻性结合起来。因为飞鸟看得更远而断言飞鸟优于青蛙,抑或是因为青蛙看得更深而断言青蛙优于飞鸟,都是不明智的。数学的世界博大而精深,我们需要飞鸟和青蛙为探索它而一起工作。
飞鸟与青蛙这个比喻是如此之妙,不由得令人怀疑,戴森这里是不是偷偷引申了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关于刺猬和狐狸的比喻,正如作家伯林(I. Berlin)曾借用它来评论托尔斯泰(L. Tolstoy)的历史观一样。笔者曾发邮件询问戴森,他取 “飞鸟与青蛙 ”这个标题,是否受到了阿基罗库斯关于哲学家分为 “狐狸与刺猬” 两种的启发?他答复说:“是,演讲的标题来自于希腊的戏剧家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他曾写过两部有名的戏剧《飞鸟》与《青蛙》,但其思想则有似于阿基罗库斯的狐狸--刺猬的二分法。我发现,对两种数学家来说,青蛙与飞鸟是更好的比喻”。
戴森在文中举出了青蛙与飞鸟的诸多例子,如培根(F. Bacon)与笛卡尔(R. Descartes)、伯西柯维奇与外尔(H. Weyl)、冯·诺依曼与曼宁(Y. Manin),并含蓄地将他本人与杨振宁作为另一对比较的例:
在做了伯西柯维奇的几年学生之后,我来到普林斯顿并结识了外尔。外尔是典型的飞鸟,正如伯西柯维奇是典型的青蛙。我幸运地与外尔在他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之前有一年的过从,从该研究院退休之后返回他在苏黎世的老家。他喜欢我,因为那一年我在《数学年刊》发表了关于数论的论文,在《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量子辐射理论的论文。他是当时对这两门学科都是行家里手的少数人之一。他欢迎我到高等研究院,希望我成为像他那样的飞鸟。令他失望的是,我不过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青蛙。
过去的五十年是飞鸟的艰难时期。即使在艰难时期,也有飞鸟要做的工作,而且飞鸟们表现出了攻克困难的勇气。外尔离开普林斯顿后不久,杨振宁从芝加哥来到普林斯顿,并住进了外尔的旧居。在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家中,杨作为一个领头的飞鸟接替了外尔的位置。当外尔还活着的时候,杨和米尔斯(Robert Mills)发现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杨-米尔斯理论 (按:外尔于 1955 年去世,杨-米尔斯论文 1954 年发表),这是对外尔早期规范场思想的绝妙推广。
第一段话跟前面所引的戴森追忆奥本海默的话何其神似!真是难以想象,年仅 25 岁的戴森能同时被数学界的领袖外尔和物理学界的首脑奥本海默如此垂青!要知道,作为外尔在物理学方面的传人的杨振宁,毕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不知道曾经近在咫尺的外尔,原来一直都对规范原理念念不忘!杨振宁曾写道 [6]:
在物理学家中,没有人知道他[外尔]对规范场思想的兴趣是锲而不舍的。无论是奥本海默还是泡利,都从未提及这一点。我猜测他们也没有把我和米尔斯 1954 年发表的论文告诉他。如果他们告诉了他,或者他偶然发现了我们的文章,那么我能想象得到,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而且会非常激动。因为我把他所最珍爱的两样东西——规范场和李群——放在一起了。
杨振宁的遗憾真可以用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来形容。这里的 “你” 就是飞鸟外尔。飞鸟与青蛙的比喻凸显了杨振宁与戴森的差别,正如杨振宁曾借用狐狸与刺猬的比喻来彰显中国近代两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与陈省身的不同 [7]。
戴森在这个演讲稿中还以开玩笑的方式建议了一种攻克黎曼假设的可能途径(转而考虑拟晶的枚举与分类)。可以看出,戴森一直没有放下他年少时的梦想(证明黎曼假设),就像屈原所说的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由于戴森对冯·诺依曼的工作(例如博弈论与计算机理论)很有兴趣,2010 年 5 月,他受邀在布朗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漫步在冯·诺依曼的花园” [8] 的通俗报告。从两个演讲的标题 “漫步在冯·诺依曼的花园”和“漫步在拉曼纽扬的花园” 可以看出,戴森倾向于将数学视为一种智力上的消遣。也许,数学在他眼里,与其说是一种智力拼搏,毋宁说是一种探险猎奇。
戴森仍然不时地回到纯数学研究中。2012 年,将近九十岁高龄的戴森还在数学刊物《拉曼纽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分拆与巨正则系综”的论文,还与普雷斯(W. Press)合作在《国家科学院进展》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研究论文。不过戴森认为,他自 1990 年以后的那些数学与物理研究更多的是具有趣味性,而谈不上特别的学术性。他在为《科学的面孔》写的自传中说道 [9]:
大多数科学家把科学当成一种类似于盖房子或者烹饪的技能,少数科学家把科学当作哲学探索。我属于前者。我从不关心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否重要。纯数学领域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与原子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重要问题同样有趣。
今年 5 月,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森的一本新书,收集了他所自选的 1990-2014 年期间的代表性文章,书名就叫《飞鸟与青蛙》[10]。这可以看作他 1996 年的《论文选集附评注》的续篇,但其侧重点跟《从爱神到盖娅》一样,收入的大部分是通俗文章而非专业论文。
本节注释
[1] Dyson 1996. Selected Papers of Freeman Dyson with Commentary.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2] Dyson 1972, “Missed opportunities”, Bull. Amer. Math. Soc. 78 (1972), 635–652.
[3] 戴森 1982.
[4] 见 这篇演讲至少有 4 个中译本。例如可见:《数学译林》2010 年第 1 期赵振江的译本(网上有电子版);《数理人文》2014 年第 2 期赵学信的译本《鸟与蛙》。
[5] Dyson 1988. Infinite in All Directions. 有中译本《全方位的无限》. 李笃中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6] C. N. Yang 1985. Hermann Weyl’s contribution to physics. 收入 C. N. Yang 2013.有中译文,《外尔对物理学的贡献》,收入杨振宁 2008.
[7] C.N. Yang 2013. 杨振宁在该书 188 页写道:伯林(Isaiah Berlin,1900-1997)普及了希腊关于哲学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观念:“狐狸掌握多门技艺,而刺猬则精通一门绝技。”我想这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来描述华罗庚与陈省身的不同:华罗庚兴趣广泛,对数学的几个不同分支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陈省身则专注于微分几何一个分支,但他革新了这个分支,并且这个革新后来对 20 世纪的几何、代数、分析、拓扑各个主要分支都有深远的影响,甚至深入影响了近 40 年来理论物理学的发展。
[8] 见有两个中译文:《漫步Johnny von Neumann 花园》,段柳柳、刘瑞义译,《数学译林》2014 年第 2 期;《漫步在冯诺曼的花园:天才的落英缤纷》,赵学信译,《数理人文》2015 年第 3 期。
[9] M. Cook 2005.
[10] Dyson 2015a. Birds and Frogs: Selected Papers,1990-2014. World Scientific. 对该书的一个介绍可见,林开亮,大科学家笔下的大物理学家——戴森《飞鸟与青蛙》,《中华读书报》,2015 年 8 月 5 日,第 13 版。
六、科学人文写作
1975 年,斯隆基金会邀请戴森写一本科学自传。在考虑如何回复时,戴森想起了老师哈代的话:“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应该写书。”于是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这引出了他的处女作《宇宙波澜》,1979 年出版。戴森曾说,他的生命是从 55 岁开始的,因为在那个年纪他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自那以后,戴森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各占一半。戴森作为作家的名望很快赶超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名望。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译成中文的书外,颇具影响的还有《生命起源》、《武器与希望》、《从爱神到盖娅》等。因其杰出成就,戴森获得了 1996 年的享有“诗人科学家”美誉的托马斯奖(Lewis Thomas Prize)[1]。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他最重要的著作《宇宙波澜》,该书曾以七种语言被翻译,中译本就有两个。书名 “Disturbing the Universe”,取自于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名作《普鲁弗拉克的情歌》。据戴森给笔者的回信,书名的含义是:我们未来的活动将改变宇宙的命运。1993 年,戴森为邱显正翻译的《宇宙波澜》专门写过一篇很精彩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2]:
本书从浪漫的角度来看科学世界,把科学家的生活比作个人灵魂的航程;它有意略过每个科学家生活、工作所在的机构,以及政治、经济的既定框架。在科学史上,团体与个人是等量齐观的,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侧重于机构与团体的活动。本书特别强调个人,因为我希望写点新鲜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对科学的浪漫观点虽然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却是真理中不可或缺的重点。
比起美国和欧洲的读者,中国的读者也许更习惯于把科学视为一种集体创作的事业;因此,我也很高兴将我个人的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如果你不觉得我笔下的故事新奇又陌生,没有发现它与你习惯的思维方式有所差别,那么就枉费了本书写作的初衷了。
本书于十四年前在美国付梓,之后我又陆续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了四本书,然而《宇宙波澜》仍然是我的最爱。它是我的第一本书,字字发自肺腑,比其他几本书投注了更多的心血和情感。如果我的著作只有一本能流传千古,而我又有权选择哪一本的话,我将毫不犹豫选择这一本。
《宇宙波澜》想必能够流传千古。因为戴森兴趣广泛,人生阅历丰富,本书读起来颇有趣味。书中第六章专门回忆了他与费恩曼 1948 年为期四天的阿尔伯克基驾车之旅,途中与费恩曼的反复讨论,使戴森终于对费恩曼的路径积分方法(也称 “对历史求和”)有了深刻的领悟。戴森与费恩曼的结伴同行,起初只是一个偶然的局部事件,但对戴森和费恩曼两个人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深刻改变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整体面貌。戴森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幸运的际遇。(令人费解的是,费恩曼本人似乎忽略了戴森对他的影响,他很少提到戴森。)
这些年来,戴森一直笔耕不辍。除了写书以外,他还写了许多有趣的文章。例如,1955 年,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成员赫尔曼·外尔逝世,戴森为英国的顶级科学刊物《自然》撰写了一篇简短的讣告,转述了外尔作为一个大数学家的价值观 [3]:
他[外尔]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努力把真与美统一起来;当我不得不作出抉择时,我常常选择美。”[4]

1988 年,费恩曼过世,戴森根据他从前写给双亲的信件编辑了一篇回忆文章《费恩曼在一九四八》(见 Dyson 1992)。
近些年来,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大物理学家相继去世,而新世纪的到来又轮到许多大物理学家的百年诞辰。许多与戴森有过交往的,例如泡利(1900-1958)、费米(1901-1956)、狄拉克(1902-1984)、奥本海默(1904-1967)、贝特(1906-2005)、特勒(E. Teller,1908-2003)、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10-2005)、克默尔(1911-1998)、惠勒(J. A. Wheeler,1911-2008)、萨拉姆(1926-1996)等,他都写了回忆文章。
戴森还不时地为《纽约客》与《科学美国人》撰稿,也常常为新出版的各类科学著作写序言和书评,因此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纽约书评》中。2013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森的书评集 The Scientist as Rebel 的中译本 [6]。就在最近,戴森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评集 Dreams of Earth and Sky [7]。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科普书,其实很多都有戴森写的书评,如美国科普作家瑞德(C. Reid)的《希尔伯特》[8],格雷克(J. Gleick)的《牛顿传》[9] 与《信息简史》[10],理论物理学家格林(B. Greene)的《宇宙的结构》[11],费恩曼的女儿米雪·费恩曼(Michelle Feynman)编辑的《费曼手札》[12],法国数学家埃克朗(I. Ekeland)的《最佳可能的世界》[13],英国传记作家法米罗(G. Farmelo)的《量子怪杰:保罗·狄拉克传》[14]。如果译者能将这些优美的书评一并翻译过来附在中译本中,想必会令读者颇受教益。
本节注释
[1] Lewis Thomas ,1913-1993,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他的许多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如《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等。关于 Lewis Thomas Prize 可进入维基百科获得详尽了解。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两位数学家首次摘取了这一桂冠,他们分别是斯图尔特(Ian Stewart)和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
[2] 戴森 1998.
[3] Dyson 1956. “Obituary : Hermann Weyl”, Nature 177: 457-458. 戴森在给《自然》投稿时曾注明:“I asked four people in Princeton who are better qualified than I am to write it, all of them excused themselves, and so I ended by writing it myself.”(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 Faculty Files / Box 37 / Weyl, Hermann 1946-1993.)
[4]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汪曾祺(1920-1997)曾表达过一个类似的见解: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5] 左边的裸女代表 Truth(大概是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右边穿衣服的代表 Beauty。整个设计受到了济慈(John Keats)名诗《希腊古瓮颂》的启发(余光中译):美者真,真者美——此即尔等 在人世所共知,所应共知。
[6] 戴森 2013. 《反叛的科学家》. 肖明波、杨光松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7] Dyson 2015b. Dreams of Earth and Sky. New York Review Books. 中译本《天地之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8] 袁向东、李文林译.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7 年. 戴森的书评见 Science 27 November 1970: Vol. 170 no. 3961 pp. 965-966.
[9] 吴铮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戴森的书评有中译文《老牛顿,新印象》,收入戴森 2013.
[10] 高博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年. 戴森的书评 How We Know,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0, 2011. 收入 Dyson 2015b.
[11] 刘茗引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 戴森的书评有中译文《弦上的世界》,收入戴森 2013.
[12] 叶伟文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 戴森的书评有中译文《智者》,收入戴森 2013.
[13] 冯国苹、张端智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戴森的书评 Writing Nature's Greatest Boo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9, 2006. 收入 Dyson 2015b.
[14] 兰梅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戴森的书评 Silent Quantum Geniu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5, 2010. 收入 Dyson 2015b.
七、结 语
作为数学家,戴森的数学能力毋庸置疑。但他并不以数学家的身份特别骄傲。在他看来,有些数学家过于离群索居缺乏人情味了。他之所以后来与妻子胡贝尔离婚,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数学疯子,沉湎于数学不能自拔,甚至置子女于不顾,而且从来没有被点醒过,不像戴森年少时被母亲点醒那样 [1]。1958 年,戴森与马拉松长跑运动员艾米(Imme Jung)结婚。戴森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儿,唯一的儿子乔治(George Dyson)是著名的科学史家。


戴森的数学生涯与剑桥数学学派特别是哈代有密切关联,正是哈代与赖特合著的《数论导引》引发了戴森对数论长达一生的兴趣。应该指出,虽然戴森学习和吸收新东西的能力很强,但他在大学两年时间里学的数学其实很局限 [2]。正如戴森在给笔者的信中曾说起的,他的老师哈代和李特尔伍德作为英国的数学领袖甚至阻碍了英国数学的进展:
哈代和李特尔伍德是旧式的数学家,他们虽然活在二十世纪,做的却是十九世纪的数学。他们虽然做出了漂亮的工作,但他们对源于法国和德国的新的抽象思想没有兴趣。结果是,年轻一代的英国数学家,包括我,在一个远离繁荣于法国的新数学的环境下成长。
事实上数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哈代和李特尔伍德忙于研究经典数学(解析数论与古典分析),导致了英国下一代的数学家没有及时跟上抽象代数与几何拓扑兴起的现代数学潮流。在当时的剑桥,只有霍奇是唯一的例外。他不仅跟上了现代数学的步伐,而且就在戴森入学剑桥的前后做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戴森并不为霍奇的讲课所吸引。所有这些,导致戴森对数学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戴森的数学视野和品味也就局限于哈代、李特尔伍德与拉曼纽扬的范围之内。但这些人的工作(解析数论与离散数学)都偏离主流数学太远了。特别是拉曼纽扬的工作,体现的是一种奇异美,简直就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拉曼纽扬那里,你根本看不到历史和传统,拉曼纽扬就像是他的同胞诗人泰戈尔(R. Tagore)诗句 “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中的飞鸟。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追寻他的足迹是前途渺茫的。这种横空出世的数学确实难以为继。(当然,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拉曼纽扬遗失的笔记(Lost Notebook)当时尚未发现。)
戴森虽然早期在数论研究中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他对纯数学中这种曲高和寡的冷清氛围不满意,于是决定离开纯数学而转向应用数学。他在《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3] 一书的导言中写道:
在我后来的科学生涯中,我并未忠于哈代的理想。起初我步他的后尘进入了数论领域,并解决了几个数论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优美但无关宏旨。后来,在我作为数论专家工作了三年之后,我决定做应用数学家。我认为,比起继续证明只能引起一小撮数学家感兴趣的定理,理解自然的基本奥秘要令人激动得多。
作为物理学家,在很早的时候,由于费米的提点,戴森认识到,做物理研究不能仅仅靠纯粹的数学演算,更需要物理直觉的指引。戴森很清楚,他缺乏物理直觉。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功得益于与物理学家的广泛交流,得益于他的数学品味和才能:他以数学家的价值观来做物理。
他在 1964 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上的文章《物理科学中的数学》[4]中写道:“数学之于物理,不仅是计算现象的工具,更是创造新理论的概念和原理的主要源泉。” 有如共鸣,杨振宁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5]:
我的大多数物理学同事对数学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崇拜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巧妙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神乎奇迹的是,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但是,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有不同的价值观,戴森的价值观并没有得到物理学家的广泛认同。这与数学家对他的看法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数学家不认为戴森的数学工作很重要,但愿意听他的数学见解(例如当代著名数学家阿蒂亚(M. F. Atiyah)在他的第五卷《论文选集》序言中就提到了曾从与戴森的交谈中受益);而物理学家认可戴森的物理成就(例如他荣获了 1981 年的沃尔夫物理学奖),但拒绝他的数学价值观。
戴森在《不合时尚的追求》[6]一文中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他将数学物理这门学科的宗旨理解为,用纯数学的严格风格和方法来理解物理现象;而数学物理学家的目标则是,澄清那些作为物理理论奠基石的概念的精确数学意义。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数学物理学家,戴森得到了高度认可。在 2012 年的世界数学物理学家大会上,戴森获得了该领域的最高奖——国际数学物理协会颁发的庞加莱奖(Henri Poincaré Prize)。
然而,不论是作为数学家还是作为物理学家,戴森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唯有作为作家的戴森,才算是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如果要从二十世纪的数学家中挑选出一百位最有成就的数学家,戴森基本不能入围。因此,他年少时想成为二十世纪《数学精英》系列人物之一的梦想势必要落空了。而作为物理学家,虽然他早在二十五岁就名扬四海,但他从来也没有期望自己成为像他的同事杨振宁那样的伟大人物。
一直以来,物理学家好像都对戴森有更高的期许,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教授、1977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在对谢尔维(P. F. Schewe)为戴森所作的传记 [7] 的书评 “一个多面手的生涯(An iconoclast's career)” 中写道:“戴森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并且成就很大,然而,如果他术业有专攻,又会是怎样呢?” 这大概是在期待戴森成为 “刺猬” 或 “飞鸟”。但应该指出的是,戴森的广泛兴趣与丰富想象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很能综合的人,人们也期待他成为一个能够总揽全局的人,但其实他首要的身份是数学家,更擅长的是分析和小心求证。
也许戴森在二十世纪的数学界和物理学界不能占有特别高的地位,但作为科学家中的作家,他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戴森曾回复笔者,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哈代,因为他为非数学专业的读者写出了优秀的书籍《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哈代的写作确实吸引人,这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历过数学史上最浪漫的传奇,发现了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家拉曼纽扬,所以写作也富有激情。不过,哈代的言论比较极端,一旦绝对化,就会创造出一种奇异的美感和坚不可摧的力量,令读者往往不自觉地信以为真。例如哈代在其辩白中曾写道:
只有少部分数学有用,而即此少部分也较为乏味。“真正”数学家的“真正”数学(无论其为“应用”数学或“纯粹”数学),即费马(Fermat)、欧拉(Euler)、高斯(Gauss)、阿贝尔(Abel)、黎曼的数学,几乎全部无用。如能解释真正数学的存在,则应解释为艺术。
这一点哈代有点像他的同胞王尔德(Oscar Wilde),另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天才。又因为哈代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他慧眼识出的天才拉曼纽扬又英年早逝,所以他暮年提笔时,处处洋溢着悲观情绪,这也许在无形中打动了某些读者。但他的有些话是经不住检验的,比如他说 “费马、欧拉、高斯、阿贝尔、黎曼的数学几乎全部无用” 就错得离谱 [8]。
对于写作和数学研究,哈代完全是以美为至高法则。他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写道:“美是首要的试金石:丑陋的数学不可见于天日。” 可以说哈代是一个 “纯” 到了极致的数学家,比外尔还要纯。笔者曾在通信中问戴森,真与美二选一,他会选择哪一个。他回复说,不同于哈代和外尔,他只是在做研究时会优先考虑真实,而在讲故事时则会优先考虑美妙。
相对而言,戴森的文字则不时闪现着睿智与幽默,其评判也较中和,对于有可能看起来矛盾的说法,他能通过玻尔的互补性原理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为哲学基础来调和。而且,戴森的视野要比哈代开阔。他早年读到的凡尔纳、托尔斯泰、韦尔斯(O. Wells)、霍尔丹、赫胥黎(A. Huxley)、奥威尔(G. Orwell)的作品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像那些前辈一样,戴森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与洞察力。此外,戴森在写作中常常旁征博引,特别是戏剧和诗歌——这是自小受父母熏陶和中学时代受弗兰克影响的结果,为其作品增色不少。例如,在《宇宙波澜》一书的索引中,你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和作家的名字,如奥登(W. H. Auden)、布莱克(W. Blake)、歌德(J. W. von Goethe)、弥尔顿(J. Milton)、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和叶芝(W. B. Yeats)。戴森在《生命起源》中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因为即便他所作的猜想或预言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布莱克的名句(引自A Vision of the Last Judgment)早就让他释然:To be an Error and to be Cast out is a part of God’s design [9].

哈代与戴森的共同点,也许可以用培根的名言来概括:“如果没有奇特的奇异性,也就没有与众不同的美。” 而如果要指明戴森与哈代的差别,也许我们可以窃取哈代本人的话 [10]:
假如真的能把我的雕像塑在伦敦广场的纪念碑上的话,我是希望这座碑高耸入云,以至人们见不到雕像呢,还是希望纪念碑矮得可以使人们对雕像一目了然呢?我会选择前者。可以想见,戴森 [原文是斯诺博士(Dr. Snow)[11]] 会选择后者。
笔者曾经问戴森是否同意后面这个说法?他表示同意。事实上,戴森在《从爱神到盖娅》一书的序言中说 [12]:“我所有的作品,其目的都是打开一扇窗,让高居科学庙堂之内的专家望一望外面的世界,让身处学术象牙塔之外的普通大众瞄一瞄里面的天地。” 他成功了。

戴森的著作不仅给读者以亲切感,更给人以他作为科学家的强烈使命感。也许我们可以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屈原的一句话来评价作为作家的戴森:“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
本节注释
[1] D. J. Albers, “Freeman Dyson: Mathematician, Physicist, and Writer”, The College Mathematics Journal, Vol. 25, No. 1 (1994), pp. 3-21.
[2] 一个明证可见戴森的论文“The Threefold Way. Algebraic Structure of Symmetry Groups and Ensembles in Quantum Mechanic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3, No. 6, 1962, pp.1199-1215),文中指出“三重方式”根源于经典的 Frobenius 定理(实数域上的可除代数只有三种:实数、复数和四元数),而这一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教授伯格曼向他指出的。Frobenius 定理是抽象代数中的基本结果,可惜戴森在剑桥上本科时对此闻所未闻。
[3] 有两个中译本《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 覃方明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21 世纪三事——人文与科技必须展开的三章对话》,席玉苹译. 台湾: 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9.
[4] 戴森 2007. 《物理科学中的数学》,收入克莱因(M. Klein)编《现代世界中的数学》,636-656 页. 齐民友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5] C. N. Yang 1983.
[6] 戴森 1981. “Unfashionable pursuits”,有中译文《不合时尚的追求》. 袁向东译.《数学译林》1985 年第 2 期. 电子版可见清华大学数学系周坚教授的个人主页~jzhou/Buhe.htm
[7] P. F. Schewe 2013. Maverick Genius: The Pioneering Odyssey of Freeman Dyson. Thomas Dunne Books.
[8] 特别的,哈代的得意门生、日后成为 MIT 数学系主任的莱文森(Norman Levinson)曾撰文反驳,见“Coding Theory: A Counterexample to G. H. Hardy’s Conception of Applied Mathematics,”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77 (1970): 249--258.
[9] 铸成错误并被摈弃,亦属上苍精心设计。
[10] 哈代 2007.
[11] 斯诺(C. P. Snow, 1905-1980),英国化学家兼作家,尤以 1959 年所作的《两种文化》的演讲而著称。
[12] Dyson 1992.
致 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杨先生对初稿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戴森通过邮件对笔者提供了不遗余力的帮助,还特别为本文提供了照片。作者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还得到了苏珊·希金斯(S. B. Higgins)女士、江才健先生、陈关荣教授、汤涛教授、丁玖教授、欧阳顺湘教授、葛墨林教授、周坚教授、肖明波教授、张淑娥教授、刘云朋教授、赵振江教授、付晓青教授、崔继峰博士、张海涛博士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相关阅读:《大科学家笔下的大物理学家》
链接:
文章来源于好玩的数学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