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读而思
现如今,天眼FAST、LAMOST等中国的大型天文观测装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带动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不断向苍穹追问宇宙的奥秘。可以说,尖端科学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观测宇宙的方式,现在望远镜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观测。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就在四十多年前中国现代天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一套计算机程序需要用纸带输入、手摇运行,动辄花费三个星期得到一组解……也正是那时候科研人员的坚持,为今日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021年5月,83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天文学系创系系主任陈建生院士向北大天文学系的博士生们讲述了那个时代的科研故事,并带我们一窥这五十年来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处缩影。
受访、自述人 | 陈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天文学系创系系主任)
采访、整理 | 傅煜铭、王超、余捻坤、庞宇萱、郑沄、段晓苇(北大天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校对 | 吴学兵
提供 | 陈建生、吴学兵
责编 | 韩越扬、吕浩然
40多年前的中国天文研究,计算机程序要靠穿孔纸带摇出来
少年时代与北大岁月
我出生在福州一个很穷的家庭,父亲在我大概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所以也没有能力去挣钱。那时候她在私人纺织厂里给人家纺纱,勉强过日子。我的童年时代可以说是很不开心的。由于福州两次被日本人侵占,我经常看到日本人非常残忍地屠杀、虐待中国人,甚至我的母亲也被日本人拉去修建飞机场。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国家太穷才受人欺负的思想。
我1951年从上海回到福州,1952年进入格致中学(当时叫福州第五中学)。中学时代是我一生当中最开心的几年。因为那时候念书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又没有很大的高考压力,我们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
1956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那时的中学生来说是影响很大的。一方面,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我们年轻人也都有为祖国科学的繁荣昌盛做贡献的大志向;另一方面,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6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全国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个伟大的成果,两个华人科学家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们当时都立志要报效国家,在中学念书也很有朝气。那时候的学生不觉得学习枯燥,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还组织了各种兴趣小组,所以个性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我们几个好朋友,也是学习好的几个同学,经常一起讨论一些梦想和人生大事,所以我觉得那段日子过得是非常开心的。
1957年,我考取北大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因为知道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满怀希望到北大来念书。但是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大概到了大学五年级我们才真正开始上课。物理课程的四大力学本来应该在二三年级就上完,但实际上到了五六年级才开始学习。
我虽然在北大念了6年,但实际上真正学习的时间算下来不到两三年。所以这6年时间我们没念多少书,也没多少时间念书。即使有这样的遗憾,但我对北大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她是我的母校,毕竟北大6年也是我整个人生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陈建生院士大学时代在北大(1960年)
投身北京天文台建设
1963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前身)工作。当时,北京天文台还没有正式成立,叫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为什么叫筹备处呢?因为当时从法国回来一个天文学家,他叫程茂兰,原来在法国上普罗旺斯(Haut-Provence)天文台工作,科研做得很好。他1956年回国后觉得中国天文台太少,当时只有一个紫金山天文台。而且,紫金山天文台在南京,下雨天、阴天很多,不适合做天文观测。所以程茂兰回来后觉得应该在北京地区建一个天文台,因为北方的天气条件在全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他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天文台,需要学生。当时只有南京大学有天文系,该系的学生毕业后都被近水楼台的紫金山天文台要去了,基本上很少有毕业生到北京这边来。
程茂兰跟北京大学当时的副校长周培源讨论能不能在北京大学办一个天文系,于是就把原来物理系我所在的班全部转成天体物理专业。我们就开始学天文学,后来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北京天文台。那时候天文台刚刚筹建,我们从(当时的)东德定了两台光学望远镜用来建天文台。第一件事情是要找好的台址,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后在天文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选台址的工作。
选台址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需要考虑晴夜数、海拔、大气视宁度等因素。先要进行普选,选出好的候选台址之后进行2-3年的常规观测,再决定最后的台址。在我去之前,老一辈的天文学家已经做好普选工作了,他们在河北省找了两个候选台址:滦平和兴隆。
我们去以后就开始做定点观测了。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年的春节就是在兴隆山上过的。我们要去半山腰挑水,需要把供应的物资用毛驴拉到山上,冬天还要把半山腰的冰块砸开取水。每天要定点观测:晚上八点一次,半夜两点一次,凌晨天快亮的时候一次。大学毕业生和其他老同志都是轮流来观测,一次观测一个月,过两三个月再去观测一次。
所以我从1963年毕业到1965年,基本上就在做台址观测、选台址。后面又遇到十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的科研工作遭遇了各种坎坷,直到1976年后才逐步回归正轨。幸好,我们报效国家的理想最终还没有泯灭。
走出国门,开始前沿研究
我真正的科研工作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也是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研究人员,1979年就被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澳大利亚联合天文台(简称英澳天文台)。英澳天文台当时建了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学望远镜(AAT),3.9米口径。在这之前美国帕洛玛天文台在1949年建了一台口径5米的海尔望远镜,该望远镜在世界天文发展历史上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这个望远镜是1949年建的,整体技术、基建还比较落后。
澳大利亚AAT望远镜是1975年建的,是第一台全自动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望远镜。所以当时建成之后全世界科学家都非常吃惊。过去我们都用传统的望远镜,对准天区都要用手去摇。而这个先进的望远镜对准天体的时候,只需要在键盘上把坐标敲进去,望远镜就自动对上了目标,而且精度可以在一个角秒之内,非常了不起。
那时候大望远镜主要做光谱观测,要把天体导到狭缝上,狭缝宽度也就一个角秒左右,所以按一下回车键之后天体就自动移到狭缝上了。而过去我们拍光谱的时候,因为望远镜对得不准要花很多时间去找星。星认出来以后,慢慢把它拉到狭缝上来,一次就要花好几分钟。
英国还在澳大利亚建了一个施密特望远镜。其实第一台(大型)施密特望远镜也是美国帕洛玛天文台建的。帕洛玛天文台将具备大视场的施密特望远镜和5米海尔望远镜结合起来,先普查再精测,取得了很多成就。英澳天文台已经在澳大利亚赛丁泉(Siding Spring)天文台放了一台3.9米的AAT望远镜,再放一台跟帕洛玛天文台参数完全一样的施密特望远镜,这样南北半球各一个施密特望远镜,就完成了全部天区的巡天工作。

陈建生院士(右二)在澳大利亚工作时留影,左一为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席瓦西教授(1979年)
我1979年3月去了澳大利亚,1980年6月回到北京。1982年我又去了欧洲南方天文台(ESO),在德国也工作了一年。应该说这两次出国经历对我来说是个突变,对我震动非常大。但是在国外期间,我一边利用国外的设备做研究工作,一边心里想的最多的还是 “中国怎么办”。因为肯定回国以后这些设备都没有了,中国当时还是那么落后。
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差到什么程度,你们很难想象。首先科研人员没有办公室,我们在天文台的时候,一间30平方米屋子里40个人在那里办公,一个人面前就摆着一张桌子。研究人员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仪器,望远镜就是一台当时从德国进口的施密特望远镜,改正镜口径60公分,主镜90公分。还有一台双筒望远镜,是个折射望远镜,口径40公分。观测都是用天文底片,底片是用玻璃做的干板底片。除这两个观测设备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计算机就更落后了。
我印象当中,在1975年做双星研究的时候,我要解的轨道叫食变双星轨道,这个解的计算就要用计算机。当时国产的计算机叫DJS-21,是一个慢得不得了、体积又大得不得了的计算机。计算机的输入设备就是一个纸带输入机,有一个专门的打字机和一个专门的穿孔机用来打程序,用的是Fortran语言和ALGOL语言。一个程序打出来就是一大盘纸带,这一大盘纸带放在纸带机上面向计算机输入时就需要快速旋转。快速旋转的机器又很不好用,有时转得太快撕了纸带,前面那些程序就全报废了。为了不要重新打程序,就要补纸带。

当时的数据纸带盘(左)和计算机(右)的照片
那时候一个程序的编写通过大概要三个星期。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即使是这么简陋的机器,每个人一次也就给分配一个小时的上机时间,一星期总共给几个小时时间。上机把程序输进去以后,发现程序纸带被转纸机撕掉了就不得不退下来,当天这一小时就白费了,只能回去补纸带。
补完后好不容易又用一个小时再把程序输进去,然后机器啪啪啪打出一大堆错误出来,就必须回去修改程序的错误。一个程序总要上来下去修改五六次,这样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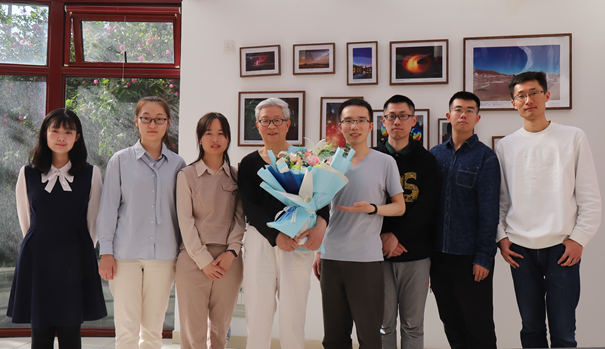
陈建生院士(左4)与采访学生合影(2021年5月)
现在你们在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上,一会儿程序就算完了。但当时中国的研究条件真的非常落后,和国外差距很大,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科研状况。
三十年前对于中国天文的思考,今日是否应验?
提出大视场、大样本天文学的战略思想
鉴于80年代初中国当时的情况,我在国外想的比较多的就是:中国天文到底应该怎么走,同时也要考虑世界天文走势会是什么样子。我这个人比较善于想一些大问题,想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我当时从国际的发展情况出发,看到了一个苗头。在说这个苗头以前,先说回到天文研究的方法。
天文观测研究从方法论上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普查性质的,一类是精测性质的。所有的学科差不多都要做这两类研究,比如说地质探矿,肯定要全国性普查一遍,了解地下大概哪些地方有矿产,然后对有矿产的地方再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普查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整个系统的性质,对典型案例的研究那就要深入了。天文研究也是这样,如果要研究整个宇宙的性质,肯定就要对整个宇宙进行普查;如果对其中的特殊天体与典型天体感兴趣,就要做精测。
当时北半球跟南半球的两个施密特望远镜就是做普查任务的,天文上叫做巡天。这两个望远镜视场(能观测的区域)很大,而且做了蓝颜色(B波段)和红颜色(J波段)两个颜色的巡天。我在澳大利亚时,曾参加过南半球施密特望远镜的巡天工作。当时每张底片拍之前为了提高它的灵敏度,要做敏化处理,就是把底片放在暗箱里面,让底片在氮气里泡24小时。拍完照以后的底片显影也很费工夫,如果显影液不均匀,底片上的灵敏度就不一样。
为解决这个问题,天文学家特别发明了一种摇摆式的槽,把底片显影液倒在槽里进行摇晃,显影液在上面飘来飘去,这样显影就很均匀。一个显影后的底片出来后,天文学家还要认真考察底片有没有缺陷,要挑那些完全没有缺陷的底片作为巡天底片保存下来,而将其余的淘汰用于一般用途。
总的来说,天文学家花了很大力气做巡天底片,但是底片用起来很不方便,尤其是要对底片做定量处理的时候。因为底片除了量子效率不高以外,还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它不是数字化的,很难用计算机处理,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底片扫描机来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底片的非线性响应。非线性响应是什么意思呢?光接触到底片以后,底片相应位置就会变黑,入射光强跟这个黑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特性曲线来表示。但实际上底片的黑度和入射的光强不成正比,这就是非线性响应。
当时的巡天底片很像字典。字典要花不少功夫来编,编完大家都要买。但是买完字典以后,天天拿着字典做研究工作的人恐怕非常少。这套巡天底片就变成了一个单位的底片库搁在那里作为资料,大家需要的时候才去查。据我所知,拿这些底片做全天研究工作的只有一个人——美国天文学家 George Abell(阿贝尔),他利用这套底片先做了北半球的星系团表,也就是著名的阿贝尔星系团;后来南半球的巡天底片出来后,他又编了南半球的阿贝尔星系团表。
而整个天文界,用这么宝贵的底片,就做了这么一项系统性的工作。之后其他天文学家也没有做类似的工作,主要原因除了底片不好用以外,还是缺乏科学上的需求,当时科学上也没有对大尺度天文学的需求。
那么,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天文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是什么呢?当时,天文学家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台4-5米级的反射式光学望远镜来做光谱观测。那个年代4-5米口径的望远镜已经是最大的了。今天我们做10米、30米口径的望远镜,那是因为我们至少在望远镜的技术上有突飞猛进的创新。当时用望远镜拍有缝光谱,每次只能观测一个天体。如果天体比较暗,或者你希望得到的谱分辨率比较高,就需要观测很长时间。
我曾经在澳大利亚观测一个类星体,要观测三个晚上,光谱的信噪比才足够。所以你想想当时全世界就5台大望远镜,一年也就观测几百个天体,怎么能够做大尺度天文学研究呢?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那个时候天文学家的兴趣主要是做恒星,因此恒星物理发展很快。可以专门去研究那些特殊的恒星和典型恒星,通过对它们的光谱观测来研究其物理性质。大部分望远镜都是做这类工作的,连观测星系的都不多,而且就算观测星系也是观测比较亮的,最远的星系还不到0.1的红移(距离地球13亿光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文学上有四大发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有机分子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四大发现里类星体和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是影响最大的。
类星体的发现打开了整个高红移宇宙研究领域的大门。现在我们普遍接受宇宙的寿命是137亿年,约等于140亿年。如果我们把140亿年归一化成100年,把宇宙整个进程都按100年来算。恒星就是宇宙年龄100年时的天体,那么红移为0.1的星系差不多90岁。所以类星体发现之前我们只能掌握90岁到100岁的宇宙信息。而类星体是当宇宙只有2岁时的天体。观测类星体就可以了解宇宙从两岁开始到100岁的信息。有这么大的时间跨度,要研究的问题就多了。
而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则被认为是大爆炸宇宙学最关键的观测事实。大爆炸微波背景的辐射是相当于宇宙诞生后6分钟发生的。我们可以从宇宙诞生后的6分钟开始,一直研究到它的100岁。
这样一个变化就意味着我们天文研究在战略上要发生转移了。宇宙演化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就包括宇宙到底怎么诞生、演化的?这些都是要了解的关键问题。哈佛大学天文学家赫克拉(John Huchra)和盖勒(Magaret Geller)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用一个很小的1.5米望远镜来研究星系光谱。
通过一个一个拍星系光谱的方法,他们共拍了大概2000个星系,并把这2000个星系的空间分布画出来。他们发现星系在空间分布上很不均匀,有 “长城”、“空洞”、“桥” 这些结构。所以在这个时候,有远见的天文学家,应该就意识到整个天文学研究的领域要发生重大变化了。
应该说我当时在国际上比较早地预见到这个方向的发展,所以在1985年,我就提出来中国天文研究要不失时机地转向以大尺度、大样本为战略方向的研究。而且做这个方向的天文学研究,中国还不需要造4米级的望远镜,只要做一个大视场2米级的望远镜,就可以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这就是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想到的事情。
当然,世界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想到,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想法,美国的想法就是后来的斯隆数字巡天计划,建一个2.4米口径的望远镜,做大视场巡天研究。这两个计划当时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并行地在发展。我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负责科学研究的最高领导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了我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就组织国家科委对这一巡天项目进行了论证。
BATC巡天
科委论证以后,因为宋健要到欧洲去开部长级的科学技术合作会议,他就把这个项目带到欧洲跟欧共体讨论,后来被列入中国和欧共体的正式科技合作项目。所以我从1987年开始,就忙着做这件事情,负责望远镜的设计、找台址、国际谈判,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来回奔跑。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项目也被中断了,不过我对这个方向还不想放弃。
国家天文台兴隆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口了一台中等大小的施密特望远镜,通光口径是60公分,主镜90公分。这台望远镜自从安装以来总共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是我写的,发表在《科学通报》1965年9月刊上。我对这篇文章的印象一直非常深,因为同一期刊登的还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摘要。我的文章和这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上,我感到很荣幸。

国家科委基础与高技术司组织的大施密特望远镜提案论证会(1986年)

陈建生院士在河北雾灵山为大施密特望远镜选址期间留影(1987年)
当时60/90公分这个施密特望远镜闲着没用,我就跟北京天文台台长说这个望远镜我们课题组 “承包了”。台长同意了,我就开始对望远镜做全面改造。首先探测器要改成CCD(电荷耦合器件,图像采集和数字化处理的关键器件之一),但那时中国基本上没有CCD。我就派我的好朋友魏名智到美国加州大学Lick天文台CCD实验室去工作。通过他的合作,我们要到了一片不要钱的CCD,那已经是当时市场上最大的CCD了,2k*2k像素,但是是厚片的,量子效率差一点,只有40%左右。
然后,我们就开始改造望远镜,从望远镜的传动开始改造,到焦面仪器改成CCD,后来又发展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滤光片系统。过去滤光片都装在一个滤光片转轮上,使用时将滤光片转到光路上,不要的就排到光路外面。但是我当时要做的不是几个颜色,而是19个颜色,相当于获取有19个采样点的低分辨率光谱。有缝光谱观测一次只能拍一个天体,但用我这样的光度学方法,一次可获得视场内上千个天体的 “光谱”。
19块滤光片装在转轮上挡光就很厉害。后来我就发明了一个滤光片系统,叫做 “打字机” 式,就像把滤光片放在“打字机”的端头。不用的时候“打字机” 的臂就躺在镜筒上,所以不挡光,要用的时候把它举起来,放进光路上。施密特望远镜装CCD在国际上是第一家,所以尽管这个望远镜很小,完成不了做全面巡天的任务,但至少可以做一部分有特色的巡天。这个望远镜在国际上评价蛮高的,很多朋友来看了后就很积极参与。以前这台施密特望远镜自安装后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改造后每年有将近20篇论文的产出。

陈建生院士与兴隆60/90cm施密特望远镜(1989年)
我们做的星团赫罗图,被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收录,作为标准图。这是很高的荣誉,因为赫罗图是恒星演化最重要的图。利用这套设备我们发现很多恒星演化初期产生的赫比格-哈罗(Herbig-Haro)天体,把世界上当时这类天体的样本翻了一倍。我们发现美国人发表在《自然》上一篇关于星系NGC5907的观测文章,他们认为不存在暗物质的问题。我们花了几十个夜晚的观测,把叠加起来,面亮度达到30等,与哈勃望远镜观测深度差不多。我们发现这个星系有暗的结构,引起国外的轰动。
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小行星。小行星不是我们的主课题,当时因为在天文昏影和晨光这两段时间不适合做比较深的曝光,就拿来做小行星。我们做了三年小行星观测,没想到发现量在全世界排第三。我们用CCD和一套先进的寻找小行星的计算机程序,效率非常高。后来因为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小行星望远镜运转起来了,我们就停止了小行星的项目。即便如此,我们三年里发现了2000多颗小行星,现在很多命名的小行星都是我们发现的。
这个望远镜到现在还在工作,已经观测了差不多三十年。最近又改去做超新星巡天,效率也很高,每年大概会发现50颗超新星。当时这个望远镜改造后,引起了台湾地区和美国一些天文学家的兴趣,来参加我们的合作,这就是所谓的BATC(Beijing-Arizona-Taipei-Connecticut)巡天。这套设备解决不了宇宙演化这样的大问题,但是培养了一批中国做大样本天文学的人才,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会用大样本来做天文研究的人才。
BATC巡天的数据库也是中国第一个被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国际天文数据库收录的数据库。我在1997年后基本上不管BATC巡天的具体事务,因为那时我的社会任务太多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社会任务很繁重。我的接班人周旭把BATC巡天做的很好,做的比我还好。

BATC巡天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合影(2013年)
说起我这一生,我觉得做的最重大的事情就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对大样本天文学的贡献,应该说我在国际上还是很早预见到天文领域的方向变化,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世界上都非常重视巡天工作了。美国十年规划里,排在地面天文学第一个优选项目,就是造一台8米级的地面巡天望远镜 LSST。
空间项目排在第一位的是做一台叫WFIRST望远镜,现在已经改名叫Nancy Grace Roman Space Telescope,也是大视场的红外巡天望远镜。目前 LSST已经基本快建好了,WFIRST的状态跟我们中国空间站望远镜状态差不多。欧洲最优选的项目也是大巡天,说明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宇宙演化需要大样本。
除了类星体和微波背景辐射,还有两个对天文学发展影响很大的重大发现,一个是暗物质,一个是暗能量。暗物质实际上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发现了,但天文界普遍认可的还是七十年代由 Vera Rubin 通过观测星系旋转曲线证实了暗物质的存在;暗能量是九十年代被发现的。
这两个发现当然更加大了对大样本天文学的研究力度。因为无论是暗物质也好,暗能量也好,都是一种大尺度现象,所以这些问题都变成世界最重大的难题了。在美国《科学》杂志 “世界100大科学难题” 排名中,暗物质、暗能量都是排在前列的,它们是全世界科学家都关注的问题。现在,大的巡天项目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觉得研究方向的战略转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代表着整个学科方向的转变。
对中国天文,我做过的两件重大事情、发现的三个问题
重视人才培养,推动大学天文学科发展
除了对中国开展大样本、大视场天文学的一些贡献,我自认为做的第二个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推动大学天文的发展,这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1997年以后,我实际上承担很多社会工作,第一线的科研已经做的不多了,主要指导研究生和年轻人在做。我的关注点就转到大学天文,因为我深感一个国家天文学的发展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大望远镜,这是必须的;另一个是人才,没有人才什么也谈不上。
中国的天文人才是非常匮乏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真正有天文系的大学,只有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北大天文系那时还没有,只有地球物理系的天文专业。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两个天文系,这怎么可以呢?而且北大是中国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里天文系都没有,这在世界上是说不过去的。世界上所有顶尖的大学都有天文学科,所以我非常关心北大天文学科的建设。
我是北大天文专业毕业的,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专业办了几年就基本停止。中间偶尔招生,等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退休的教师多了,没剩下几个人。当时乔国俊、吴鑫基老师也快退休了,乔国俊老师来找我,说能不能帮帮北大天文专业?我说当然可以。
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首先筹建了一个中科院跟北京大学的联合天体物理中心,就是北京天体物理中心。这个中心成立的时候很隆重,我记得那天邀请了(时任,下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北大校长陈佳洱,最难得的是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也参加了。成立仪式很简单,签署协议合办北京天体物理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每年还出Annual Report(年报),主办了很多学术会议,开拓了很多研究方向。

陈建生院士与北京大学、广州大学部分青年教师合影(2007年)
2000年,北京天体物理中心成立两年后,我就动员北大成立了天文系。当时校长是许智宏,他很支持,聘我做系主任。我把天文系定义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天文系,是两个单位合办的,我就等于代表中科院来出任天文系系主任。
天文系刚开办的时候,人是很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引进人才,期间从国外引进了4个人:一个是吴学兵,现在的天文系主任;一个是刘富坤,也当过系主任;还有刘晓为和范祖辉。4个年轻老师加入到天文系后,大大改善了天文系的师资状况。
后来,我又促成美国科维理(Kavli)基金会与北大合作,在2006年成立了国际化的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从全球招聘所长和师资,并成立由国内外著名学者组成的理事会和科学咨询委员会,对研究所的运行和发展给予指导。这一新体制研究所成立后吸引了很多海外优秀的青年学者加盟,使北大天文学科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同时我还致力于招生。北大最大的优势是本科生,因为全国最好的中学生都要考北大清华,所以我们必须把本科生培养做好。北大天文系成立后每年独立招生30名本科生,但两年后因天文系合并到物理学院,学校停止了天文系的单独招生。大部分学生在物理学院都学物理了,导致学天文的很少。
所以,后来我就要求恢复天文系独立招生,但学校以通识教育、大类招生为由不同意,我跟学校说我们要办的必须定位是小而精的一个系,要办精品,学生是关键。经过三年停招后,学校到第4年终于同意天文系独立招生。独立招生后我怕生源不够,就在2008年发起全国中学生天文夏令营,针对的对象就是刚上完高二、暑假后进入高三的优秀中学生。
当时北大还有政策,通过夏令营可选拔推荐优秀中学生,高考时可获得加分,这样就很有吸引力。天文夏令营办起来后在国内很有影响,后来又与国家天文台、北师大天文系和北京天文馆联合举办,到现在已经办了13年了。学生报名参加的越来越多,甚至多达上千人。但因为规模限制,每年只能招收100个夏令营学生。
在夏令营里我们给学生讲课,组织参观天文台站,开展各种活动,最后通过笔试面试考核来选拔优秀学生。采取这个方法我们吸引了一批喜欢天文的优秀中学生报考国内大学的天文系,也改善了北大天文系本科生的生源质量。

陈建生院士等与2010年全国中学生天文夏令营同学合影(2010年)
除北大外,我还很关心全国的大学天文。因为光北大天文系办起来还不够,所以后来广州大学也想办天文来请我帮忙,我就答应了,并从2003年开始举办京广天体物理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主要是帮助培养广州大学的师资和学生。这个京广会也办得很成功,后来参加的单位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扩展为京广厦会议了,包括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都参加了,已办了十三届,越办越好。
去年我又提出来,以后京广厦会议能不能以学生为主来办?让学生们去办他们自己喜欢的会议,老师只给予帮助,特别是资金、学术上要给帮助。今年的一届将在中山大学举行,由学生们自主筹划组织,自己考虑这个会议怎么开。这既是对学生的锻炼,也是鼓励他们早一点成长起来。
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联合国定义2009年为国际天文年,理由是纪念伽利略在1609年第一次使用望远镜观察宇宙之后400周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为纪念国际天文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了一次纪念大会,有3000人参加,要我做主题演讲。
我在演讲时除了强调大型望远镜的国际合作外,另外一条就是人才问题。而且我讲中国天文的人才问题光靠中科院是不能解决的,因为中科院只有5个天文台,人员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我们需要的人才不是几十个,是成千上万,天文人才的培养就只能靠大学。
2009年我做报告的时候,全国大概有2000多所大学,但当时有天文学科的大学只有5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在2000所大学中只占2.5‰,这个比例太小了。在美国差不多重点大学都有天文,比例占1/3。所以我说能不能提出一个希望,经过10年努力,我们把2.5‰增加到1%,即有20所大学。
10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也确实差不多20个大学有天文学科了。而且一些名牌大学,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办起来了。现在像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也要建,大都是中国985大学。所以一下子我们到了1%了,但1%够不够呢?其实不够。
前不久在国家天文台举行的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和国家天文台科学中心的揭牌仪式上,要我做一个报告,我就讲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占 “天时、地利、人和”。“天时” 当然不用说了,是科学需求,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巡天重要;“地利” 我也讲了,正是技术的进步使得这样的大科学工程成为可能,包括探测器、大数据、还有航天技术等。所以,“天时” “地利” 是没得说的,现在还面临“人和”的问题,就是人才队伍。
中国空间站望远镜数据量是非常大的,每天下来的数据都将是TB量级的,数据分析不是几十个人、上百人能解决的,需要上万人来解决。所以,我认为大学发展到1%有天文学科还是不够的,我希望能够再通过10年努力,能从1%变成10%。如果能实现的话,我们就有希望。这是我所做的大学天文方面的事情,也是我后一半人生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天文发展仍面临的问题
中国天文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突飞猛进。从设备上来看,我们有一些即使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望远镜,比如说LAMOST(郭守敬望远镜)。LAMOST是大样本的思路,同时也是一种时域巡天的思路。另外FAST(中国天眼)已经建成,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项目,就是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望远镜。
空间站望远镜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2009年开会时说要做一个空间望远镜,我马上就建议这个望远镜必须要做大视场巡天。我的看法是,现在是大巡天进入空间领域最佳的黄金时代。前不久我在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科学工作联合中心和国家天文台科学中心的揭牌仪式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 “光学巡天的黄金时代”。
我讲到对于地面巡天,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们错过了机会,后来美国斯隆(SDSS)望远镜做了,现在LSST也将开始做。但是空间上的光学巡天还没开始做,而空间巡天又太重要了。因为它可以达到比地面巡天好一个数量级的像质,所以如果有机会能够做空间巡天,意味着中国天文进入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代。

陈建生院士在国家天文台作报告(2021年)
如果我们利用空间站望远镜能够拿到17500平方度的高质量巡天数据,所能产出的成果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哈勃望远镜有一幅产出很多成果的图,几乎全世界天文学家都知道。这幅图差不多有10平方角分大小。而我们空间站望远镜的巡天面积比它多500万倍,我们能够出多少成果?同时,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要建一个12米的地面光学大望远镜。中国天文要发展,这些重要观测设备都是很必要的。
对现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我有几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国家天文台现任台长也找过我,我给他提了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中国天文发展缺乏一个非常权威的、被国家认可的规划。我曾经担任过中科院天文规划委员会的主席,知道做这个规划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主要是因为本位主义。规划委员会里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带着自己领域的色彩。规划委员会很难做出一个不受这些专家个人背景影响、站在国家利益上的规划。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到现在还没想出办法。
缺乏科学的规划以后,整个领域发展就显得无序。比如从中国天文的布局来看,现在射电天文的分量占得很重。而且我认为现在实际上射电天文设备的国际主流,已经不是做单口径望远镜,因为单口径望远镜有它克服不了的缺点:口径大可以提高灵敏度,但解决不了空间分辨率和视场小的问题。
目前国际射电领域发展方向是综合口径,做天线阵。望远镜有三个大指标,一是灵敏度,二是空间分辨本领,三是视场。天线阵可以把这三个指标都予以满足,所以像SKA(平方公里阵列)是国际上的一个大方向。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发展规划,是中国天文今后发展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大瓶颈就是国际合作。大望远镜建造费用动辄都是几亿到几十亿美元的量级,而且技术非常先进,对台址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中国还没有较好的台址,技术储备也达不到国际水平,仅中国一家出几十亿美元来做设备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可是中国在大望远镜建设的国际合作道路上阻碍却很多,首先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我经常听到的话是,我们中国出钱建望远镜,为什么要建到外国土地上?一些人不知道大望远镜一定要放在世界最好的地方,还需要全世界技术力量的整合,需要共同努力来造一个全世界共享的望远镜。接受不了这种国际化的思想,这是很大的障碍。
国际化问题不光是表现在设备上面,还包括我们的研究机构,比如说,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外国人非常少,而北大的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可能是中国天文界外籍学者最多的单位。但是大学招生和教研人员招聘,基本上都还是中国人来应聘,外籍的很少。我们的口号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做的还不是国际一流的事情,国际一流必须是国际化的。而在中国实行国际化,还需要在相关政策上多加考虑,解决好外籍人员的很多实际问题。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天文发展面临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规划问题,一个是国际化问题,再一个就是人才问题。人才问题要不解决,我们没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天文发展的瓶颈。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中国天文要想有大发展的话,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