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pixabay
撰文 | 周叶斌
近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公布了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的27岁男子特里·霍根 (Terry Horgan) 的详细死因,去年10月,霍根在接受基于CRISPR的研究性治疗时去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受CRISPR基因编辑治疗的患者。
3岁时,霍根确诊了DMD,自此后,这家人致力于攻克这种疾病,2017年,霍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哥哥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治愈罕见疾病”,为弟弟及更多的罕见病患者的疾病寻找治疗方法。2019年,霍根的哥哥联合MIT与耶鲁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团队,为他设计出了定制版本的GRISPR疗法。3年后,FDA同意他们将这项疗法用在霍根身上。

Terry Horgan。图片来源:Cure Rare Disease官网
2022年8月,霍根作为第一位接受CRISPR疗法的患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参与这场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正式参与实验,死亡随后而至,根据后期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怀疑,霍根的死因是基因治疗中高剂量重组AAV引发的先天免疫反应。
今年的10月12日,在“治愈罕见疾病”的网站上发布了纪念他去世一周年的文章,文章说:“特里是一位先驱者和战士,他想帮助找到治疗他可怕疾病的方法……”
霍根的故事是这个地球上最著名的,患者参与临床试验的故事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现代社会,患者们勇于打破边界,更踊跃、更密切地参与到临床试验的标志之一。
被医学专业化排除在外的患者
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研究出自个人兴趣爱好:牛顿不是经过专业培训成为物理学家的,达尔文也不是一路读本科读博士做博后当PI变成生物学家。但19世纪末后,科技的飞速发展让科研变得更为专业化,也让做科研成为一项高度职业化的行业。
医学研究领域更是因为涉及到人身安全,变得高度分工专业化。例如某个疾病的新药研发,往往是经过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多年的基础研究积累,专攻药物研发的药企才会介入,尝试研发药物,之后又需要经历多年、多个临床试验,确认药物安全有效后,才有希望上市。
在这一过程中莫说非专业人员难以找到插手的机会,就算是专业人士,往往也只是起了类似螺丝钉的作用:严格来说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药,再杰出的科学家也只是庞大研发机器上或大或小的一部分。
如此专业化、高度分工的机制有其必要性。例如一个新药能成功,不仅需要药物针对的致病机理“准确”,还需要这个药物在一系列理化属性上靠谱。该分子能不能被人体有效吸收?吸收后稳定性如何?除了作用于我们想针对的药物靶点,是否还打击到了别的蛋白质,是否会因此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
几乎没有哪位研究人员可以回答上述所有问题,它们都不局限在某个领域。只有通过横跨多个专业的广泛合作才能解决新药研发过程里的各种难题。
新药研发甚至都不仅靠科学家或医学专家来引导。高度复杂的药物研发过程意味着研发成本也在急剧攀升,这需要管理、金融背景的人来思考资源分配,是否还应该继续某个分子在某种疾病里的开发,对药企来说绝非只是科学问题。
但在高度复杂化的药物研发里,有一个利益最为相关的群体却经常被排斥在外,或者说被固定在一个偏远的角落,那就是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们。
“被试者”——作为背景板的参与
疾病研究以及新药研发当然需要患者群体参与,不过在如今的科研体系下,患者与患者家属们的参与方式往往被高度限定:研究对象、临床试验的志愿者。
一方面,绝大部分患者及其家属不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来更深入地参与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医学伦理也倾向于将患者、患者家庭拒于千里之外。因为他(她)们对相关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考量,很难保持现代医学研究所必须的客观。此外,这也是出于对患者的保护。不难想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企业会利用患者对新的治疗方案的渴望,做出伤害患者利益的事。如几年前引发巨大争议的贺建奎转基因婴儿事件,所利用的,正是HIV感染者家庭希望做试管婴儿又希望孩子健康的心理,从而“招募”到了志愿者来参与一项对这些家庭来说毫无必要的违规冒险。
也是因为非常清楚患者群体在专业知识上与科研人员的不对等地位,如今,大量的科研规范是在要求药企、医生与研究人员与病患们保持距离。
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效果并不差。像引发癌症治疗革命的免疫治疗,经历了长期的基础研究、药企研发,通过科学家、医生、药企研发人员、FDA等药品监管机构的各司其职,极大地改善了包括肺癌、黑色素瘤在内的多种致命癌症患者的预后。
新冠mRNA疫苗也类似。mRNA递送技术以及基于蛋白结构的抗原设计,这两大关键基础在新冠暴发前就通过多年研究有了一定积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尽管药企、政府监管机构用各种方式加速了疫苗研发,一切也不过是在过去的基础科研之上进行,某种程度仍属于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但并非所有疾病的药物研发都能在当下的科研机制下顺利。罕见病,特别是那些发病率极低的疾病,往往不能获得研究人员、药企的重视,或者无法“适应”传统的新药研发中的“规则”。
为了改善这种缺医少药的现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属不再满足于医药研发中的背景板角色,而是正在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科研之中。
今年,《华尔街日报》记者Amy Dockser Marcus出版的新书《We the Scientists: How a Daring Team of Parents and Doctors Forged a New Path for Medicine》就以一种极为罕见的遗传病:C型尼曼匹克氏症(Niemann–Pick disease type C,NPC)为例,讲述了多位NPC家长逐渐以平等合作伙伴的姿态,与科学家、医生乃至监管机构交流合作,为自己的孩子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为未来的患儿寻找新药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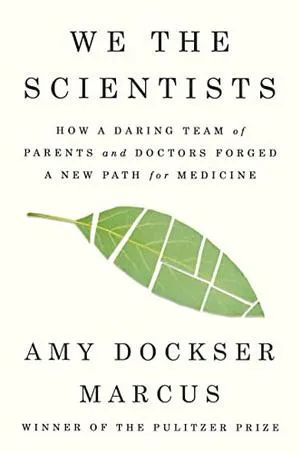
We The Scientists 图书封面
罕见病,患者参与的突破口
罕见病在当下的医药研发里遇到困境并不意外:罕见这一特征就足以让罕见病在传统的疾病研究、新药研发路线里处处不适。
例如,现代新药研发强调研究的严谨性,当一个病人用了某个药情况好转,科研人员需要区分这是因为该药确实对该病有治疗作用,还是仅仅源于偶然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现代医药研发,我们很自然会想到大型的双盲对照临床试验,因为那是确定药品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金标准。
但对一些罕见病来说,由于患者人数少,招募到足够的患者做有统计意义的临床试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例如《We the Scientists》一书中的C型尼曼匹克氏症,一些家长在发现孩子患病后得知全美国总共只有200多位患者,全世界也只有500多位孩子不幸患病。
如此少的患者,别说开展临床试验困难重重,甚至连很多基本的疾病研究都很难进行。患者家属与医生会发现该领域很多研究因为研究人员只遇到了个位数的患者,研究往往也只局限在单个医学中心的几位患者。这样的研究结果具有普适性吗?能推广到更多患者身上吗?没人能下结论。
患者少与研究不足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科学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药研发更是如此。如果有大量的研究积累,我们更容易明确疾病的致病机理,有哪些薄弱环节可以去攻击。而想研究一种药物对C型尼曼匹克氏症是否有效的科研人员以及想将另一种罕见病药物用到C型尼曼匹克氏症的药企却会发现,这种致命遗传病的病程、症状都缺乏足够的研究。我们知道它是特定的基因突变导致胆固醇异常积累,继而引发神经元死亡,患者会有包括神经系统发育迟缓在内的各种症状。可是病人的症状发展是什么规律?当一个孩子表现为吞咽困难,另一个则表现为说话不流利,是否意味着前者的疾病进展更快,病情更重,还是,这只是个体差异?
当这些最基本的疾病规律都不被知晓时,就算有一个新药可以进入临床试验且招募到一些患者,我们又如何判断这个药是否起了作用呢?我们甚至连判断疾病恶化或缓解的标准都没有!
这些患者对研究的投入,不计成本
即便是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医药研发,患者群体也不时展现出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时期,由于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与歧视,药企与监管机构都行动迟缓,正是患者们的努力推动才催动了HIV抗病毒药的发展。
不同于当年艾滋病患者们做的更多是呼吁政府、产业界、研究人员关注他(她)们罹患的疾病,如今,越来越多的病人组织开始更深度地参与到疾病研究甚至药物研发之中。例如ALS的患者组织为很多研究出钱出力。2022年获得FDA批准的ALS新药Relyvrio背后就有ALS病人组织的大力支持。
在一些罕见病中由于传统医药研发方式面临的挑战,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患者家属开始直接下场参与。例如美国企业家Martine Rothblatt因为女儿确诊没有有效治疗药物的肺动脉高压,创办了United Therapeutics。Thomas Gad看到得了神经母细胞瘤的女儿通过刚上市的免疫治疗(GD2单抗药物)后得以存活后,建立了Y mab公司,专门推进神经母细胞瘤的新药研发、上市。

Martine Rothblatt。来源:维基百科
对罕见病的研发来说,患者或患者家属无论是以倡议者的身份还是更深度直接参与,带来的最大贡献或者说最大变化,应该是他(她)们的坚守。
对于传统药物研发的各个参与者:研究人员、医生、药企、医药监管部门,某个药物的研发只是一项工作。如果一项工作不成功,那么就换一项,甚至在开启某项工作前,他们还会考量成功的概率,如果概率过低,不如根本就别做。
上述流程能部分地解释很多罕见病的研究不足:科研人员不愿意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绑在一个没多少人关注也很难拿到经费的冷门领域,药企不愿意进入一个即便成功商业回报也因患者极少而非常有限的方向,监管部门很难对一个知之甚少的疾病提出合理的管理标准。
但患者与患者家属们不同,他(她)们不会去考虑另一个更容易申请经费的领域,也不需要向投资人解释为什么投入一个小众市场。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她)们都有一般研究人员、药企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无法匹敌的动力,去坚持投入直到成功。在《We the Scientists》中,曾经讲过一对父母持之以恒地在每个凌晨4点收集孩子的晨尿样本,并送到他们认为应该需要这个样本的实验室的故事。
对于很多被传统科研圈忽视的罕见病来说,患者与患者家庭的这种执着与韧性恰恰是最宝贵的。像《We the Scientists》书中的多位C型尼曼匹克氏症家长,努力查找任何可能的治疗线索,不断与研究人员沟通,甚至找寻学术会议里与FDA官员交流的机会。这些努力也带来了许多进展,包括一些药物的同情用药数据收集以及临床试验开展。
患者的激情与科学的底线
当下的科技进步促使患者及其家人能更容易地介入到科研之中:互联网的兴起让非专业人士也能迅速查找到大量科研信息,而社交网络又让很多病人得以互相交流,团结凝聚成一个个自发的患者群。
但患者组织深度参与研发也有潜在的“风险”。他(她)们的立场、思维模式可能与科研传统有冲突。例如,对于科学家们来说,研究疾病、寻找潜在新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所作的一切往往是为了未来的患者,并不指望能立刻帮助当下的病人。可对患者家庭来说,他(她)们有更强的急迫性,会希望立刻就能有药物可用。
这就可能带来研究路线上的冲突。《We the scientists》一书也描述了同样致力于推动C型尼曼匹克氏症药物研发的家长与科学家间的分歧甚至争执。例如,一个叫cyclodextrin的药物在动物实验里展现希望,家长们期望能尽快将该药物推进到临床实验中,而科学家们则认为需要更多研究才行。
患者组织与专业人员在药物获取渠道上产生分歧非常常见。如前文所言,罕见病患者与家属会希望有机会尝试新药。但科学家会考虑新药也可能有未知的毒副作用,轻易让患者试药,蕴含着巨大风险。此外,当你考量的不只是眼前的病人,而是未来这个疾病的所有患者时,你也会变得更谨慎。
比如,随意扩大尚缺乏证据的药物使用人群,很多患者在不是严格控制、科学记录数据的临床试验下接受治疗,这不会帮助我们积累药物有效性的数据,甚至会阻碍临床试验的进行——患者会选择不参与临床试验而直接用药。最终可能让必要的科学验证变得更为缓慢,延缓药物上市。

来源:Pixabay
如何让患者组织——包括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更好地融入科研圈,成为不仅地位平等,也有正面推动作用的伙伴,或许是未来罕见病的科研人员、药品监管机构以及患者组织本身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让我们能针对极为罕见的疾病开发出药物,例如,一些核酸药物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到彻底的个性化订制,即便一个疾病只有一位患者,也可以设计出药物。但如何明确这样的个性化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又如何推动此类患者极少的药物研发?这些关键问题远未解决。
我们面对的罕见病也逐渐分化为两类。有的罕见病患者人数虽与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比要少很多,但凭着监管机构孤儿药认证带来的优待、药品支付方在价格上的通融,已经能吸引到足够的科研、产业投入。比如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 SMA),发病率约万分之一,如今不仅有基因治疗、反义寡核苷酸(ASO)以及传统小分子药物三类治疗方法,每一种也都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类罕见病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市场化路线,在现有的科研、药物开发机制下可以做到市场的正向激励。
可是像C型尼曼匹克氏症这样全球患者只有几百人的罕见病,从研发到药品审批都还有太多缺陷,也更需要患者组织的深度协助。我们需要他(她)们的倡议来督促科研机构开展相关疾病的研究,也需要他(她)的协助来设计、开展必要的临床试验,甚至需要参考他(她)们的意见来寻找更适合这些疾病的药品审批灵活度。
在这一过程中,科研人员、监管机构需要做的不仅是学会倾听患者组织的意见,也需要学会把握科学底线。在一些罕见病中我们已经能看到部分药企试图靠患者讲感人故事的方式逼迫监管机构放松审核标准。推动这些罕见病的研究需要患者、患者家属的坚持与激情,但如果我们沉溺于感性之中,忽视科学所需的客观性,那么最终也会伤害这些患者、患者家庭。
随着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患者、患者家庭更直接地介入医疗研究会越来越普遍,而医药研究的传统参与者,从科研人员到药企再到监管机构,也需要学习一项新课程:患者可能将不再单纯是服务对象,而是对等的合作伙伴,我们不能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宣称会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要学会如何与这些最有热情与毅力的合作伙伴相处。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