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Michel H. Devoret。图源:耶鲁大学。
撰文 | 晓旭
● ● ●
十余天前得知我的导师Michel Devoret获得了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初的惊喜褪去后,我被一种平静而持久的感动占据。
我在 Michel 的组里工作了六年。他作为科学家的气质与方法深刻塑造了我——既在学术上,也在私人层面。某种意义上,我漫长而迟来的青春期,直到博士毕业后的某个时刻才真正结束,而这期间,Michel 是影响我最大的人。
他获奖之际,我写下这些关于 Michel 的片段,向他致以由衷的祝贺与感谢,也为这份影响做一次回溯。
01
科学家永远诚实
第一次见到Michel是博一的冬天。当时我刚刚从一年半的gap year中慢慢稳住阵脚,开始联系可能收我进组的导师。我的首选是做量子信息实验的两位重要学者,也是长期合作者:Michel Devoret和Rob Schoelkopf。录取后的开放日我和Rob聊过20分钟。他充满活力,自信友善,也是我本科论文导师David Schuster的博士导师。短暂的交流让我对Rob印象很好;但正式联系导师时,仍在动荡中的我与这样外放的活力有些错位,便先联系了还未谋面的Michel。
我先后给他发了两封邮件都未得到回复。寒假将尽时,我守在他办公室门口,做最后努力。终于某天见到他,他让我进屋,简单聊一聊。
这次谈话简短而出人意料。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没想好,只好回答:“实话说(To be honest),我不确定。”正想给出更多解释,他随即打断我,带着法国口音和一点点狡黠:“我不喜欢美国人常说的‘To be honest’,这句话仿佛在说你不是一直诚实。但科学家要始终诚实。”
他又微笑地问:你为什么会被录取?我疑惑。他解释说,量子信息近两年很热,录取难度越来越大,每个人被录取都有一些理由。比如你是不是跟领域内教授工作过?我回答我的本科导师是Dave。他说:那就是了,他的推荐信应当是你被录取的原因。
他又问:你小时候是不是会经常拆收音机、拆闹钟的那种人?我说对,经常拆了装不上。Michel说好,暑假的时候我的组里会有一个空位,你可以这学期先来听组会,暑假可以开始实习。
这便是我和Michel第一次见面。他的气质让我感到一种清醒的吸引力,但我也不确定自己为何顺利进组。几年后跟他再聊起“面试时的什么特质最能预测日后的科研表现”,他只说:他也想了很久,后来发现面试时很难看出来,最终还是要在工作中看他们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而我进组时恰逢同届的另一个学生实习不合格没能留下,我大概是因缘际会地填上了那个位置。
02
“努力的风格”
博一暑假和博二上学期,我和高年级博士生Clarke一起工作,学习基础知识,因此与Michel交流不多。博二下学期,有一次他在实验室里巡看,走到我的桌子前问进展。我打开实验记录的文档,给他看当天刚刚测量到的数据,跟他说新电路的某项指标出奇的好,也许说明新设计确实有用。Michel看着图,说不错,然后指出图中横轴的单位应该用另一组数据做归一化,并简要解释了原因,随即离开。当时我并未在意他的提醒,只想收集更多能彻底表征“新现象”的数据。
几天后我在走廊又遇到他。他问我近况。我随手打开笔记本电脑给他展示新的进展。他翻到一张与前次类似的图,说:“好像我上次没能说服你,这里横轴应该做归一化。”他又补充道:“哪怕是实验笔记,每幅图也都该达到论文水准。”
这是很多人和Michel共事时的首要印象——他对细节要求极高。坐标轴的尺度和单位、颜色在色彩空间中的关系、衬线体与非衬线体的选择、对基本物理量的约定取舍,这些涵盖极广的细节都在他的关注之中。如果一个人在组会(甚至百来人的大组会)给报告时犯这些错误,他也会直接打断指出。
我一度将他大多数要求理解为对细节的洁癖,对某些特定约定的坚持则视为他的小怪癖。直到后来一次闲聊,我才意识到这背后是他思考后的主动选择。
那时是博二的暑假,我刚结婚。Michel问我妻子在做什么。我说她最近在做一个心理学实验,研究儿童在不同年龄对“努力”和“结果”的价值倾向。她发现,年龄小的孩子几乎一边倒地偏向奖励结果,社会化之后(约十岁开始)又一边倒地奖励努力。这类触及“人如何构筑价值的凭据”的问题,我也一向感兴趣。
我问Michel更重视努力还是结果——我以为他会回答“结果”,毕竟成功如他,多半是结果导向。他几乎没有停顿,说他看重的既不是结果也不是努力本身,而是“努力的风格”(style of effort),也就是“如何用力”——他关注在每件事情都用最合适、最讲究的方法用力。
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独特,想追问其中深意,挖掘出某种哲学观点。他却接着补充道:人生哲学还是要和每个人的性格相称。他觉得“关注努力的风格”和自己性格十分契合,一向相信并实践,幸运的是,这也对他一直奏效。
Michel探讨这些时语气平静,像在说每日的寻常事物,只是多了一丝审视的好奇。很长时间里,这个概念成为我理解他、从他身上获取科学与人生经验的最重要的视角。
03
稳定的内在秩序
博三伊始,我要第一次在“周一午餐会”上做一小时的汇报。那是耶鲁超导电路领域的每周研讨会,对于博士新生来说算是在小圈子里正式亮相,是个大事件。
当时我与同届的学生Jaya合作,研究对transmon设计的迭代。transmon是2007年在耶鲁提出的一种电路设计,随后很快成为领域内最重要的实验器件。十年研究之后,基于transmon的简单应用已经做得差不多,更复杂的应用开始受制于非线性系统的一些内禀问题(我们当时并未看清)。Michel对此有直觉理解,与合作的理论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电路,并且在仿真中验证了部分优势。我的工作就是对新设计做实验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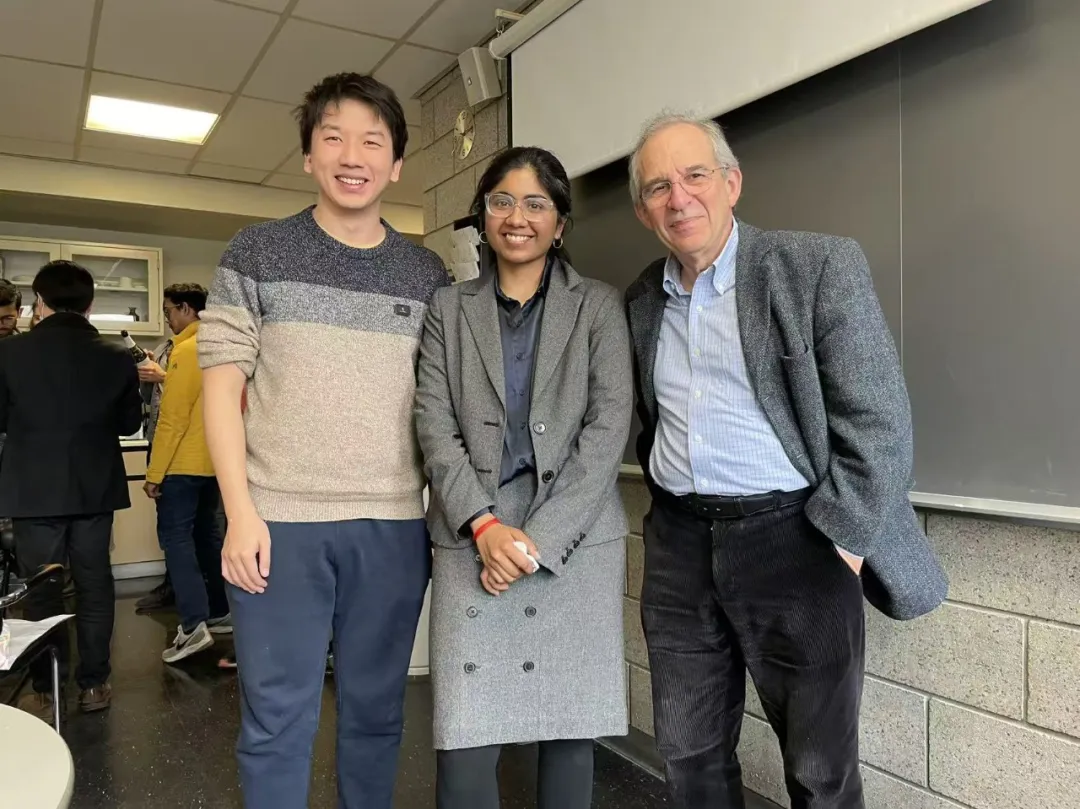
作者(左一)和Devoret在一起
经过大半年的实验,我们终于在汇报前一周拿到了第一组完整数据:在某个关键指标上,新设计比transmon提升一倍以上。接下来,Michel和Clarke多次帮我修改PPT,细致梳理问题的源起、我们的假设、新电路的设计与数据、以及下一步的验证计划。
对于低年级博士生而言,我的演讲很成功——科学态度端正、PPT精细、故事有说服力、结果令人振奋。结束后,Michel和同事们纷纷对我的工作表示祝贺。我欣喜于博士生涯以一个完美亮相正式开始,也为即将解决领域内一个重要问题感到兴奋。
我加紧推进后续实验,直到一周后的某天深夜,偶然发现数据处理代码里有一个变量一直引用错了。修改代码并重新做数据分析,果然,那个关键指标上的“翻倍”正是这个小错误造成的。
那晚我很沮丧。这种沮丧不止于希望的破灭,更在于希望的根源——我隐隐觉得,这个错误的源头很可能就是我对“好结果”的过度期待,而“周一午餐会”把这种期待以戏剧化的方式曝光了。我不安自己有一定可能会被开除——可能是因为这转折让Michel难堪,更可能因为我缺乏科学精神。但Michel说科学家要始终诚实,我别无选择,也只能当即给Jaya发信息,约好第二天一早去见他。
见到Michel后,他对这个“噩耗”显得镇定,只说:这种错误越早发现越好,现在发现胜过以后任何时候。
后来,他解释过为何对学生PPT如此严格:实验物理的细节太多,任何一处疏忽都可能把人带向错误的结论。如果他看到一个实验者的演示小错频仍,他会首先怀疑这个人是否可靠——结果再漂亮,他也会首先怀疑正确性。我当即想到那次午餐会的经历,意识到他对科研中结论的反复修正早有深入的体会,也只是把这次错误当作我科学训练的一部分。
Michel的平静让我从困扰中脱身出来。接下来几天我们反复讨论:新设计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transmon实验中的不稳定性究竟从何而来?后来证明,这个问题比它看上去难得多。我和Jaya之后五年都在拆解并回答这个问题,才在理论上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类似的互动贯穿了我的博士生涯。这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深层信任。这并非来自他的温和——事实上,他的性格很强烈。我曾几次向他提出各式要求,都被他严肃地指出不合理,然后坚决拒绝(他还向我们推荐过《唐顿庄园》,说那是“坚定且尊重地拒绝”的范本)。又有几次,合作者出于各种原因在论文未臻成熟时想匆忙发表;数次劝说未果后,Michel明确表示如果现在投稿他将退出署名——而他确实这么做过。
这种信任源自一种稳定。我发现,无论我带来的消息让他由衷地高兴还是心里一沉、无论请求是否合理,他的自我意识都稳定如一。这让他能一以贯之地表达自己的内在秩序。他会认真思考当下的情况,找到最合适的用力方式——也就是他所说的“努力的风格”——然后以绝对的坦诚告知他的想法。 一两次交锋后,这种稳定让我就获得了用同样的坦诚和他进行探索的信心。
04
迷茫与承诺
到博四上学期,我们又研究了一年多transmon中的不稳定性,知识积累愈发庞杂,理解亦登上几个台阶,觉得可写一篇论文做阶段性总结。那时我在Michel组里刚刚两年多,训练不过三分之一;可“博四”这个称呼却不断提醒我博士生涯已过半。
这个时间上的人为节点让我陷入很深的迷茫。它让我开始无法忽视:我并不能纯粹地沉浸在物理研究里,心里总有一种绕不过去的自我关切,像根细线牵着我——当时我以为这是更广泛的对人与社会的兴趣。这股牵引让我在入学前做过教育创业,但始终隔着一层,最终选择了离开。
博士生涯过半时,我不确定是否想以科研为职业,但也无从判断是否要就此退出博士项目——我从小就喜欢物理,有时也能在科研中感到兴奋和快乐,只是那种快乐好像很漂浮,缺少与自身存在相连接的重量。更困难的是,这些难以诉诸语言——每当试图解释,都和真实所感有偏差。
在这种迷茫与科研生活中拉扯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很疲惫,决定去找Michel聊聊。我并不知道期待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他作为导师有权利知道我的状态,也许他的智慧能给我启发。那时我戏谑地想,Michel像一把刻着“真理”二字的大锤,能把我所有不够彻底的解释捶碎。
决定去找他那天,他一直在办公室里和学生讨论实验。我不时从楼道走过,透过虚掩的门察看情况。九点多的时候,他来我办公室找到我,说我看上去不安,问我想聊些什么。我费力地向他解释自己的状态。
他听了后,没有直接评论我是否该退出。他说很遗憾,作为导师,对这些个人的问题他没法为我提供答案。他问我之前是否有过gap year,我说有过一年半。然后他还是问我是否考虑过再休学一段时间,想想这些问题。
随后,他又解释了他对博士生的期待:他承诺将学生训练成一个成熟的研究者——能提出好问题,并且为之找到成熟的答案。同时,他也需要学生对同一目标作出同等的承诺。我说,靠着同侪压力我应该也可以读到毕业,但我抓不住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对这个承诺很难全心投入。他听完,问了我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困惑,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论?”
这是典型的Michel式发问。我打算用什么方法论?——面对迷茫,我最好的“努力的风格”是什么?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那时所有的心神都被自身困惑和对内在议题的沉溺所占据。
那时我看精神分析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Michel的问题让我意识到,或许这是我当时能拥有的最好的工具,我只能全力用好它。不久之后,我便开始五个月的休学。那段时间Jaya承担了大量的论文写作任务,我每天划出一小时和她共同写作,其余的时间密集地进行精神分析。我家还买了一块两米半的白板,妻子和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在上面讨论,探索那些难以诉诸语言的感受。
原本背负生命之重的困惑,在密集的讨论下逐渐失去一些重量,让简单确切的自我意识开始显露出来,慢慢成型。某一天我想起 Michel 说过“能问出好问题,并找到成熟答案”,想到:如果在博士毕业时,我可以诚实地说自己成了这样的人,就足够让我对这段时光感到坦然。又想到他提到过,我和他只需对这个目标做出承诺,于是我把其余的纠结暂且放下,专心完成了余下三年的训练。后来我见闻不少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摩擦,才意识到Michel对“博士生—导师”的关系一定有过深入的思考,才能给出如此简练、恰到好处的总结。这种恰到好处,曾让我长久地忽略了它的分量。
05
博士训练的下半程
回到组里后一段时间,Jaya和我终于完成了论文的初稿(准确说,这是第二次“初稿”;第一次完成后被我们否定,并决定拆分成两篇论文重写),并和Michel逐句修订。二十多页改完,他先表示祝贺,又把结论段落重读两遍——我们在末尾揭示了一对“量子—经典”的对应关系。沉默片刻后他说,起初以为把这对对应关系清楚地“显形”已足够重要,“为何成立”可以留给后来者。但全稿改完后,他意识到,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解释并且统一这对对应关系,若没能回答,工作就尚未完成。我和Jaya交换了一个略带尴尬的笑容:这意味着研究要再次重启。那时博士已经进入第五年,Jaya和我一篇文章都未发表,但我们依然同意他的判断。
回头看,那一天标志着我的博士训练进入下半程。之前,我们更多是顺着Michel的直觉去摘低垂的果实,像学生一样对有预期的结果进行验证和打磨。那天之后,Jaya和我成为了他的同事,一起面对三人共同的未知。这也是我成长最大的阶段。
这种未知,对我的首要冲击是精神层面上的。那段日子,我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在想科研问题。每隔一小段,我不是想明白了一个要点,以为自己逼近了某个长久困惑的本质,就是得出令人沮丧的判断,怀疑所谓创新其实与物理定律相悖。几周下来,我积攒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和希望与灰心间的起落。这些反复很快耗尽了我的心力。
Michel对这样的工作状态评价为“混乱”,说这样的努力并不收敛。他的指导回到“努力的风格”——剔除所有言过其实的表达和空泛的想法,把每一件事尽力用最正确的方式做好。那段时间,我开始每隔几天就整理科研笔记本上的内容,变成一份论文标准的文档(这是休学前Michel提到的方法,但那时很快就进入了论文撰写阶段,所以只坚持了很短时间):用能想到的最好的角度确立最恰当的论题,无论大小,交代其出发点;用最好的方式分析数据、作图、推导;用最准确的词汇描述结论,用最平实的语言讨论意义。这样,每一小步都在坚实的基础上展开,并导向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下一步。这也成了我日后抵御未知所致焦虑的唯一有效方式。
那时起,Michel每几天就会跟我和Jaya讨论数小时。有时前一天九点刚结束,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又打来电话,说他想了一晚,对某个问题仍有疑问,约我们今天继续。这样的讨论占据了Michel每天工作的大多数时间,也让人最直观地感受到他开放而自律的心智:他从不为结果焦虑,而是反复讨论我们每一个小发现的表达和意义,并为由此带来的新知感到满足。当亲历一项工作以这种方式从一片模糊中开始、不断因新的认知而改变方向、最终收敛为一个深入且成熟的成果时,能让人真正体会到Michel所坚持的“努力的风格”的魅力。
Michel对我的训练虽都发生在学术语境,但在我漫长青春期的末尾,却成为我重建自我结构的关键起点。
我长久的挣扎是笼罩在身上的一种虚无感,让我不断寻找能回应它的人生体验。大学前后,我一度认为这是人类共通的存在性困境;后来在与自己反复纠缠中才看见,它其实是私人的——源于早年父子关系中长期的边界不清。追溯这个根源漫长又艰难,但即使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仍久陷于一片自我价值的荒原而不知如何重建。这种虚无感持续牵引着我,去寻找有与之相称重量的体验,一旦失败,又转向追寻更强烈、更深入的经历。
但与Michel共事时,我第一次遇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风格。他对一切煽情或自我扩张的语言具有本能的警觉,一有苗头他三言两语就能拆解掉,把注意力拉回问题本身;他对每件事的判断简洁而准确,从不将意义膨胀为存在性表述——精确本身即为充足根据,无须再被叙事化。他反复示范自己所说的“恰当用力”,劝说我也要如此,也因此,我那些原本被迫去获取意义的经历得以留在原处。这种体验对我而言新鲜而陌生:它并未立即回答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但它不可忽视的真实感被我牢牢记住,成为我此后重构自我时最可靠的参照。
06
科学是一种集体努力
Michel 对自我有一种稳定的坦然,这使他看待科学时格外节制而开阔。
记得博五的时候,我和Jaya疑虑,觉得投入的主要的精力都是在学明白其他领域,而真正的新知寥寥。Michel说,科研有时候就会如此——大量的时间先用于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和思维,反复练习、熟悉。后来那项工作逐渐成型,某天我又陷入对工作创新性的怀疑:我们研究的内核是不是早在八十年前就被发现?我们不过是在当代语境中又阐述了一遍,是否新瓶装旧酒?他说,对科学而言,在现在的研究中重新发现旧知识,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
之后有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开始不断引出更多的想法,并为组里其他几个项目提供新思路。Michel有天说,这正是一项工作成熟的表现。他伸出手,张开五指,说每项工作都像手的形状一样。我们最成熟的认知构成了掌心那片连结的部分,其他零散的知识组成了手指。一篇好的论文,应当把“掌心”写清楚——它最能经了起时间的检验,也能引发有意义的新方向——而不是沿着整只手的形状描述知识的全集。
博士临近尾声时,几篇我们看重的论文被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拒稿,有的审稿意见让我们沮丧乃至愤懑。Michel说过于原创的观点常会让人不适,我们的工作质量很好,要据理反驳。同时他又补充,决定一项工作的价值的,不是它被哪本期刊收录,甚至无关乎引用数。他说科学是一种集体努力,是所有研究者一起砌筑高楼。所以,真正定义一项工作价值的,是后来有多少研究者愿意投入他们的时间在其基础上继续。
如果回看Michel的科研轨迹,会发现他的每一代博士生都在研究一个或几个重要课题,并凭此确立自己的学术位置,很快得到领域认可;但此后不久Michel又会转向一些新的、往往尚未流行的问题。起初我把这些归因于他极强烈的好奇心。但只要你去问他,又会发现每一次转向背后都有充分理由,他始终在追问什么是“好的问题”。我后来又尝试归因于他的勇气——他从不被成就的惯性和名声所束缚,敢于放弃,敢于改变。但这个描述和他古典学者的气质放在一起,又显得太过煽情,也不准确。
对他更深的理解来自我毕业的两年后。那时组里更年轻的同事们从我们的文章出发,又做了数年的扎实的工作,完成了质量惊人的实验论文。我心里生出一种失落,像父母突然发现孩子已经成年,开启自己的生活。这些想法曾经是自我在世界上的表达,而此刻他们独立存在,之后的精彩属于它们自己的当下。那个问题又一次浮现——“当一件事脱离我而独立存在时,那曾经属于我的部分,还剩下什么?”("What remains of what was once our own", 出自 Out of Australia, David M. Halprin)这个问题在我博士之前的生活里一再出现,此刻在学术的语境中重新回来,更冷静也带着更深的重量。
那时我又想到 “科学是一种集体努力”。我知道Michel也曾站在这样的时刻面前,这句话就是他的答案。
Michel最打动我的始终是那份坦然:当话题触及自我、世界、和人与世界的连接时,他的表达总是自然而简洁,让意义止于它能承担的边界——既不把意义当作存在的凭据,也不把无意义当作姿态。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见对意义与无意义的坦然承受。也因此,他不以自我为题,把关注放回事情本身,平和地在这场集体事业中占据自己的位置,让真实继续向前。
谨以此文,向Michel致以最诚挚的祝贺与感谢。
晓旭 2025年10月18日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