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6月30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教与《单读》主编吴琦在德国展开一次深刻的对谈,围绕项飙新书《你好,陌生人》,探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分享关于 “附近” 与 “陌生人” 的思考与实践,共同思考介入式思考在当下社会的意义,这场对话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以下是本次对谈部分实录,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 ● ●
01
项飙:现在年轻人没有“打成一片”的能力
吴琦:项老师聊到的,其实还是要召唤大家重新养育自己,调动起自己能力。但其实有一点矛盾了,他们已经承受这样的后果,然后也尝到了这样的代价。
如果他幸运的话,也许他还能“活着”,他还能有他的“附近”,他可能生活在一个小一点的地方,或者不再有那么大的愿望和野心。但是这样的状况下,他还能够和那样的一个历史制度形成的结构性的困境去对话吗?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在那样的一个结构里面,他可能有什么样能动的位置吗?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可能是为了应对毒打,调整自己,结果迎来了再一次被毒打,会不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危险?

项飙:我不那么悲观。首先你说改变自己的看法,就觉得是逃避结构,逃避制度,我不太同意的。因为你活着本身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警醒,有意识地活着,有意识地观察周边,观察自己。
首先,我们今天来世上来这一遭,之前无数的人来过,在我们之后也有无数人要来,地球能存在多久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是人吗?我们其实也就是历史动态在一个时点上的临时具象而已。
所以谭嗣同可以英勇就义,跟那个时候的宇宙观可能有关系,叫以太学。全世界都是由以太构成的,你不是人,你不过这些以太聚在一块成了一个人形,当然就显然科学上没法论证。以太学是把人当做一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某一个节点上的临时具象,今天社会里面你也是一个临时具象,正因为它是临时具象,所以我们才那么丰富,因为在我的身体里面有那么多的以太要素。所以如果这么想,你现在经受到的各种的打击和不适,很可能是不同的要素在你身上还在发生矛盾和冲突,那就很有意思,这取决于你怎么样用意识来观察这些冲突。
第二个是关于社会“毒打”的想象,社会并不是就坐在那儿等着你来,然后来毒打你,然后来一个追一个,来一个打一个。
人群都是有各种癖好,这个人会打嗝儿,那个人喜欢开怀一笑,你就去观察他们。你也可以投其所好,也可以搞一把幽默。你得在那个群里面得混,我们叫混,换种说法叫打成一片。
现在年轻人这个“打成一片”,是完全没有能力打成一片,只是毒打,并没有打成一片的感觉。你的人生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以你在某一场互动当中的结果得失,来判断自己人生的意义的。你在这个过程里搏斗,在那里打成一片。
但“打”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的方式,就像尼采说你是愿意躺在水里让水承载你的重量,还是更愿意走在坚实的路上,让你自己的身体承载你的重量?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问题。但你可以选择就漂在水里头,我们叫随波逐流,那个是很爽的了。
面临艰难的时候,你的真正的生命性、主体性才会出来,也要想到任何一次焦虑都是世界在叩问你,希望你做出新的回答。所以你也可以把焦虑想象成是你主体性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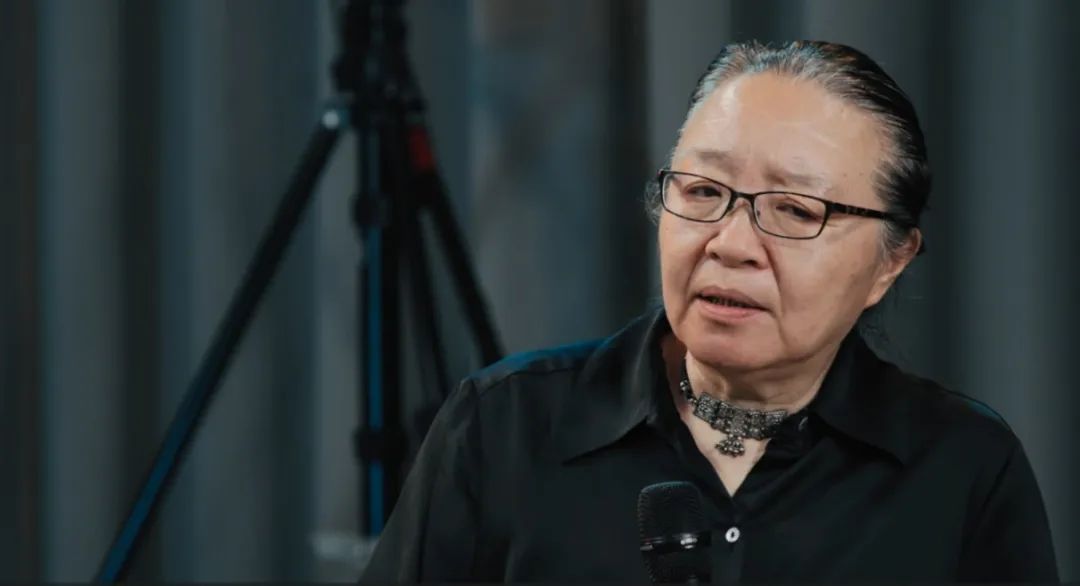
戴锦华:我们总说我们遭遇着陌生化,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求助于主体性。在我这主体始终是拉康的定义,它是个“我他”结构,当存在着“我他”关系的时候才有主体的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反回来说,我们用主体性去发现他者,这是因果倒置的一个关系。这些东西源自于话语逻辑的紧张,或者是理论逻辑的紧张。这种紧张本身其实是现实的困境。正因为我们没有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自洽的阐释,理解世界和自我的那样的一个有效的逻辑,建立起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的有效的逻辑。
谭嗣同是可逃未逃,他选择留下来挨这一刀。那是因为他自以为他非常清楚他在历史中站在什么位置上。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把自我搁置在哪怕是一个非常微观的历史当中,问题在于很多东西是无法自明地去赋予意义的。
我可以忍受我讨厌的邻居,我要承受社会的毒打,但是我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第一次开始中国式的叙述,就开始受限于短暂的个体生命。很多人喜欢刘慈欣的三体,喜欢流浪地球的设定,我们把地球开走,再找一个地球(太阳),我死有子,子死有孙,子子孙孙我们把地球开到一个新太阳旁边去。但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又精彩,现实中我们不可能会在这样的设定中。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想象当中,其实也陷在这儿了,生命就这么短暂,它和前面的接续是什么?它和后面的接续是什么呢?所以到这时候就以太学也不帮忙了这些是我观察的角度。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通过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的粗糙的理解就是最终我照见了我自己,打开了我生命的边界,延展了一点我生命边界,让我的生活变得比较有意思。
但是恐怕我们还是要把每一个微小的关系,包含我们到底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我们即便抛开资本主义,抛开阶级固化,我们也还真的要面对AI的就业威胁说。现在在国内大家都观察到,原本我们说内卷和躺平,但最近这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是欲求内卷而不得了。
就是连躺平相对于内卷都不是一个可能性,那么随波逐流就更不是可能性了。
02
项飙:跟人的对话互动,
首先要从空间出发
吴琦: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经由陌生人再到自我,进而把自我和和他人联系在一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项飙:我觉得很难去总结出一个样式或者定理,但为什么“附近”变成这么一个热词,我想也是因为大家愿意想去做一做试一试,我是觉得你只要开始互动,它就会有事情发生。
那么我的工作,不是指导大家,而是引发,一种思路上的导向。我觉得跟戴老师的对话是很有意思,主体建立过程当中的历史性和空间性,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其实是蛮注意历史的,我是比较倾向于把历史空间化。日常生活中你是很难去体感到历史的。历史进入你的时候,它是通过一些符号,但是你对这个空间的感知是更加直接的,包括跟人的对话互动,这个时候首先要从空间出发。
就说你在这一刻你怎么决定在哪个事情上多花精力,多花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感知下,会调用起很多原来看似彼此之间无关或者矛盾的一些思想资源。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提供思想与语言,通过一些意象,通过景象让大家对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够丰富起来,所做的也无非如此而已。我们是不可能提供答案,不可能提供出路。
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对主体本身建立一个叙述,而是主体的感知丰富起来,敏感起来,就够了,也是通过这次讨论,我觉得这个空间性对我是很重要的,我也刚刚意识到这一点。
吴琦:我们的生活充满忧虑,我们的工作充满内卷,对于那些依然想在人文知识领域做一点自己事的人,面对着充满AI浪潮下的失业忧虑,应该如何自处呢?
项飙:你说的可能是一个说是在传统的,比较学术的,很有积累和深度的思想工作创造出的一个公共空间,让大家一起思考。对我来讲是彼此之间是完全相通的,因为最初的这种思想和艺术,它本身都是解决人生问题。
我们90年代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个社科人文研究的专业化趋势,就是很多人觉得做研究觉得是一回事,自己过生活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今天要去打通,其实不是说刻意地要走出书斋,做一点额外的工作,其实也是把书斋本身要激活。
戴锦华:我想其实人文社会科学早就不是一个提供答案的,或者说早自我承诺可以提供答案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了。
我自己仍然回到我的很陈旧的思路上去,虽然人工智能的冲击我觉得是真实的,但是同时我又觉得是资本一定程度上在恫吓我们。换句话说,首先要否定当年的控制论的说法,就是人自有人的用处。那么不管他们的危言耸听,比较真实的它对于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需求的压缩,这一定是最真切的一个变化。
从机构的角度上说,他们要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而现在不是穷人的问题,是一些被弃之民,一些结构意义上的多余,结构意义上的冗余。人将结构性地被制造持续地被制造,一边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避免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还幸存在结构中,我们还能不能够感知这样的幸存跟结构性的放逐的联系,如果我们被赶出去了,我们还有没有图存之路,我们还有没有与世界的相互的联系的可能性?对我来说,我觉得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应该自觉的去承担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还有没有所谓毫不自恋的知识分子的社群?我们之间的相互连接和交流,在互相的询问当中互相地肯定,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实践本身不是分层的,既不是在时间上有先后,也不是在这个层级上有谁高谁低。
今天我是真的觉得为人类作为一个社群去赢得未来,时间不是那么充裕,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所以从个体到群体,从小图景到大图景,我是觉得同构性的程度是在强化,因此急迫性的程度也在强化。
吴琦:也就说只要我们还要接着活下去,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文明,可能这样所有的问题,不是只有对人文社科有兴趣的人才要面对和承担的,而是每一个作出选择和必然这样选择活下去的人都要共同承担的。
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另外一个真实人面前,你流露的困惑、情感、失落、矛盾,这些只要是真实的,它都会有一个意义。而且更安心的是那些真实的人也会看到你,你也会遇到他们,不管他们是在你的附近,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今天的对话,也希望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保持真实的对话的关系,而这绝不仅仅是仅限于我们三个。
BOOK TIME
《你好,陌生人》
项飙 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